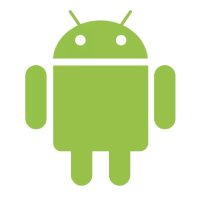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马赛曲》在德国
《马赛曲》在德国的传播几乎紧接着法国。时为一七九二年九月,离开它写成后五个月,也就是马赛义勇军在巴黎传播开来(约八月十日)几个星期之后。这一首《莱茵军团战歌》是在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宣战消息传来之夜在斯特拉斯堡写成的。在瓦尔米战役没有人唱过,而是几天之后,遵照国防部长命令,作为感恩赞美诗唱的。奥地利王子参加德军撤退谈判时听到这首战歌,表示希望得到乐谱,他收到巴黎寄给凯勒曼(François Christophe Kellermann)将军的一份抄本。《马赛曲》第一次在热马普(Jemmapes)用于战场,作曲家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这样斥责作曲者:“残忍!野蛮!我有多少兄弟不是被你杀死的!……”这句话似乎以其他方式由诗人克洛普斯托克(Friedrich Klopstock)重复过。根据一个德国传闻,一七九七年,克氏在汉堡拜访《马赛曲》作者鲁日·德·里尔(Claude Rouget de Lisle),对这首鼓舞军心的战歌表示赞赏:“你真了不起!粉碎了五万个德国好汉!”
歌德在他的《美因茨围城》(Siège de Mayence)中三次提到《马赛曲》。但很奇怪,三次之中,只有法国军队离开美因茨那一次是庄严的。其他两次,由德国士兵用双簧管吹奏,和《就会好》(Çaira)一起表演,娱乐歌德这些“正在大喝香槟的宾客”。在晚饭席上,食客要求听这首歌,“所有客人都表示满意,喜欢。”可见在德国人这边,一般人只视此歌为一首进行曲,没有人留心歌词。
弗里德兰德(Max Friedlsender)教授提供了一个奇怪的例子。一八〇四年之后,这首歌的部分旋律流入德国,本地化为歌谣(lied),迅速流行起来。变成这么个样子!侠盗歌!……《里纳尔迪尼》(Rinaldo Rinaldini),十一节歌词:
然而,正是歌德的内弟武尔彼乌斯(August Vulpius)在一七九九年,把这首浪漫曲的歌词引进他的小说《里纳尔迪尼》(Rinaldo Rinaldini)。一八〇四年,一个无名作曲家配以旋律,至今仍为德国人所演唱。不过,歌德(或者武尔彼乌斯)是否认出变成这个样子的《马赛曲》,大有疑问。如前所见,《马赛曲》以小调式段落刻入歌德记忆,而这首侠盗歌,却只使用大调式。
直到一八三〇年后,《马赛曲》才为德国音乐家所真正了解。七月革命“光荣三日”的高卢雄鸡唤醒了这首在拿破仑帝国和王朝复辟时期沉睡(或被缚住)的战歌。大家知道舒曼采用过三次《马赛曲》:一八三九年在《维也纳狂欢节》(乔装为三拍的兰特勒民间舞曲,因为梅特涅首相禁演这首歌);一八四〇年,在著名的海涅(Heinrich Heine)诗歌《两个榴弹兵》歌曲(同年,瓦格纳在巴黎把此诗谱上音乐,也采用《马赛曲》);一八五一年,在《赫尔曼与多罗特娅》的序曲。
《马赛曲》的音乐和贝多芬类似,他本该会因此如何地激动,更甚于舒曼,会在他的某一部伟大作品中高举它的旗帜飞扬。他在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从波恩到维也纳的旅途中,穿过法国军队的阵线,不是已经听到过吗?《马赛曲》完全没有进入过奥地利吗?没有撬开他那封闭耳朵的大门吗?弗里德兰德教授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发表在音乐报刊和出版物的研究中,在这方面无任何透露。然而,无论如何,贝多芬在维也纳和一些大音乐家来往,像凯鲁比尼(Luigi Cherubini),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交响乐和合唱曲起过头等作用。而他自青年时代便认识的萨列里(Antonio Salieri),在维也纳是一位权威,据说已经在一七九五年(?),一部《巴米拉》(Palmira)歌剧中采用过《马赛曲》。问题悬而未决。但是我思疑他知道这首歌,但未置一词,也没有在任何一部作品中留下它的乐章痕迹。
(刘志侠 译)
贝蒂娜谈音乐的信
这是贝婷娜致歌德的信,一八一〇年圣诞节写于柏林。
我冒昧把这篇不寻常的独白意译出来,并非没有经过踌躇。我们在里面目睹炽热的思想在黑夜里娩出。即使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专心研究过贝婷娜的文字,面对某些句子的晦涩,也承认他们的疑惑。幸好贝婷娜在一八三五年的《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Goethes Briefwerhsel mit einem Kinde)中作过解述,澄清了一些段落。我敢自认明白了全篇的精神,而我在其中得到的兴趣,令我期待阅读我的关于贝多芬著作的广大读者也同样得到。在摸索表达方式的笨拙举动下面,我们辨认出一种热烈而深沉的音乐直觉,因此我们便明白,贝婷娜在向歌德高声朗诵。
我把借用贝婷娜一八三五年的解述置于方括号内。
————罗曼·罗兰
在所有艺术和学问中,混乱和无意识是魔力的来源,在音乐里达到最高的程度,但是没有人下决心去深化。最深之处永远由学究的泯灭一切的平庸之道称霸。音乐界中,所有人都想理智地表达(而音乐的特性刚好在理智停止之处开始)。他们的这种信念本意良善,并无心计。他们不自觉地使用魔力的方式,有时只用一半,有时用错方向。那些以前冲劲十足、光芒四射的方式,现在凝固僵硬,冰冷发霉,讨厌得要命。
然而,心灵中有一种让人感觉到的秘密活动,时显时隐,不知从何而来。突然之间,天才豁然完全开放,它已经在无秩序的混沌中扩散多时,一步一步地成长……[贝多芬]。目前,音乐的状态就是这样。身在其中的天才总是孑然独立,被人误解,因为他不是在光天白日下得到成就,几乎都是不知不觉的,没有自我意识的。
必须很多人中才能出现一个天才。反过来,天才必须对人类群体有强烈的行动,并且持之以恒,否则便没有英雄。没有了大众,便没有音乐。
在过去的世纪,快感像穿过水晶那样渗入智慧中,支配作品,带领作品,令精神飞扬……在音乐方面,这已成绝响!熄灭的东西从前有过自己的庙宇,庙宇倒塌了!现在,这成了心灵的东西,音乐精神在里面回响,按照各人的性情。但是哪一位音乐家能够继续保持足够的真情和纯洁,只感觉(和只表达)好的东西?
音乐语言的命运很奇特:没有人理解!因此,世人对没有听过的东西永远激烈反对。不仅因为音乐没有人理解,还因为音乐甚至未为人所知。在音乐面前,人变得僵硬,像木头一样。他会容忍知道的东西,并非因为理解,而是习以成性:像骡子每天负重那样。我还没有遇过一个人,听了一段时间音乐后,不困倦交加地离开音乐的。这是一种必然的后果,比起相反的情况更容易理解。一个有大志的人,要是不首先从职业的自动俗套解放出来,要是他不过自己的生活,不让任何人伸手进来,他能做什么?……他当然可以“做”音乐,但他不能解放法则条文的精神。每种艺术都努力推开死亡,把人领向天国,但那里周围由没有教养的人守卫,他站在那里,头发被剃光,蒙受屈辱:本应是自由意志和自由生活的东西变成了机械,因此我们空等一场,空有信心,空抱希望:没有产生任何东西。世人要达到(这些高度的目标),只有通过现在砂泥满地的道路,通过祈祷和心灵的全神贯注,通过对上帝永恒的爱。————但是在这里,我们到达无法攀登的高岭前面。然而,只有在那上面,我们才能尝试去认识呼吸的快感……
(刘志侠 译)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