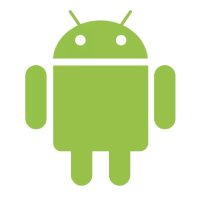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活动的是事物形像和语文(即意像和概念),离开事物形像和语文,思想无所凭借,便无从进行。在为思想所凭借时,语文便夹在思想里,便是“意”的一部分,在内的,与“意”的其馀部分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语文看成在外在后的“形式”,用来“表现”在内在先的特别叫做“内容”的思想。“意内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说法绝对不能成立。
流俗的表现说大概不外起于两种误解。第一是把写下来的(或说出来的)语文当作在外的“言”,以为思想原无语文,到写或说时,才去另找语文,找得的语文便是思想的表现。其实在写或说之前,所要写要说的已在心中成就,所成就者是连带语文的思想,不是空洞游离的思想。比如我写下一句话,下一句话的意义连同语文组织都已在心中想好,才下笔写。写不过是纪录,犹如将声音灌到留声机片,不能算是艺术的创作,更不能算是替已成的思想安一个形式。第二个误解是超于语文有时确须费力寻求,我们常感觉到心里有话说不出,偶然有一阵感触,觉得大有“诗意”,或是生平有一段经验,仿佛是小说的好材料,只是没有本领把它写成作品。这好像是证明语文是思想以后的事。其实这是幻觉。所谓“有话说不出”,“说不出”因为它根本未成为话,根本没有想清楚,你看一部文学作品,尽管个个字你都熟悉,可是你做不到那样。举一个短例来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哪一个字你不认识,你没有用过?可是你也许终身做不成这么一首好诗。这可以证明你所缺乏的并不是语文,而是运用语文的思想。你根本没有想,或是没有能力想,在你心中飘忽来去的还是一些未成形的混乱的意象和概念,你的虚荣心使你相信它们是“诗意”或是“一部未写的小说”。你必须努力使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体化,所谓确定化和具体化就是“语文化”,“诗意”才能成诗,像是小说材料的东西才能成小说。心里所能想到的原不定全有语文,但是文学须从有限见无限,只能用可以凝定于语文的情感思想来暗示其馀。文学的思想不在起飘忽迷离的幻想,而在使情感思想凝定于语言。在这凝定中实质与形式同时成就。
我们写作时还另有一种现象,就是心里似有一个意思,须费力搜索才可找得适当的字句,或是已得到的一个字句还嫌不甚恰当,须费力修改,这也似足证明“意在言先”。其实在寻求字句时,我们并非寻求无意义的字句;字句既有意义,则所寻求的不单是字句而同时是它的意义。寻字句和寻意义是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统名之为思想,其中并无内外先后的分别。比如说王介甫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中的“绿”字原来由“到”,“过”,“入”,“满”诸字辗转过来的。这几个不同的动词代表不同的意境,王介甫要把“过”“满”等字改成“绿”字,是嫌“过”“满”等字的意境不如“绿”字的意境,并非本来想到“绿”字的意境而下一“过”字,后来发见它不恰当,于是再换上一个“绿”字。在他的心中“绿”的意境和“绿”字同时生发,并非先想的“绿”的意境而后另找一个“绿”字来“表现”它。
语文既与思想同时成就,以语文表现思想的说法既不精确,然则“内容”“形式”“表现”之类名词在文艺上究竟有无意义呢?
既明白这问题,我们须进一步分析思想的性质。在文艺创作时,由起念到完成,思想常在生展的过程中,生展的方向是由浅而深,由粗而细,由模糊而明确,由混乱而秩序,这就是说,由无形式到有形式,或是由不完美的形式到完美的形式。起念时常是一阵飘忽的情感,一个条理不甚分明的思想,或是一幅未加翦裁安排的情境。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它是作品的胚胎,生糙的内容。他从这个起点出发去思想,内容跟著形式,意念跟著语文,时常在变动,在伸展。在未完成时,思想常是一种动态,一种倾向,一种摸索。它好比照像调配距离和度数,逐渐使所要照的人物形像投在最适合的焦点上。这种工作自然要靠技巧。老手一摆就摆在最适合的距离和角度上,初学有时须再三移动,再三尝试,才调配得好。文艺所要调配的距离角度同时是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语文,并非先把思想调配停当,再费一番手续去调配语文。一切调配妥贴了,内容与形式就已同时成就内容就已在形式中表现出来。谈文艺的内容形式,必须以已完成的作品为凭。在未完成之前,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几经变更;完成的内容和形式大半与最初所想的出入很大。在完成的作品中,内容如人体,形式如人形,无体不成形,无形不成体,内容与形式不能分开,犹如体与形不能分开。形式未成就时,内容也就没有完全成就;内容完全成就,就等于说,它有了形式;也就等于说,它被表现了。所谓“表现”就是艺术的完成;所谓“内容”就是作品里面所说的话;所谓“形式”就是那话说出来的方式。这里所谓“话”指作者心中想要说的,是思想情感语文的化合体,先在心中成就,然后用笔记录下来。
作品无论好坏,都有一个形式,通常所谓“无形式”(formlessness)还是一种形式,坏作品的形式好比残废人的形貌,丑恶不全;好作品的形式好比健全人,体格生得齐全匀称,精神饱满。批评作品的形式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完整的有机体。有机体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亚理斯多德所说的有头有尾有中段,一是全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互相连络照应,变更任何一部分,其馀都必同时受牵动。
这标准直接应用到语文,间接应用到思想。我们读者不能直接看到在作者心中活动的思想,只能间接从他写下来的语文窥透他的慰想。这写下来的语文可以为凭,因为这原来就是作者所凭借以思想的,和他写作时整个心灵活动打成一片。思想是实体,语文是投影。语文有了完整的形式,思想决不会零落错乱;语文精妙,思想也决不会粗陋。明白这一点,就明白文学上的讲究何以大体是语文上的讲究,也就明白许多流行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论──例如“形式重要抑内容重要?”“形式决定内容,抑内容决定形式?”之类──大半缺乏哲学的根据。
附注:这问题在我脑中已盘旋了十几年,我在诗论里有一章讨论过它,那一章曾经换过两次稿。近来对这问题再加思索,觉得前几年所见的还不十分妥当,这篇所陈述的也只能代表我目前的看法。我觉得语文与思想的关系不很容易确定,但是在未把它确定以前,许多文学理论上的问题都无从解决。我很愿虚心思索和我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