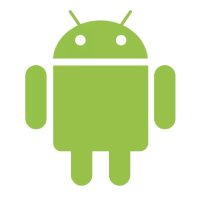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本篇颂文,由第八颂至第十六颂,如第一章科分。)
第一章能变差别门
论文一:如是已说第二能变,第三龙变,其相云何?颂曰: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了境为性相,善不善俱非。
讲解:前面讲完了第二能变的第七末那识,那么第三能变的前六识,它的义相又是怎么样呢?《唯识三十颂》颂文曰:‘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了境为性相,善不善俱非。’颂文的意思是:然后是第三能变,它有六种差别,其特点是了别外境,其性质包括善、恶、无记三性。
本篇九章颂文,其中包括了九个题目,就是诠释前六识,是以七段九义来科分,七段又称七门,其科分如下:
一、能变差别门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体别门
二、自性行相门了境为性————————————————————————————————————自性门
相————————————————————————————————————行相门
三、三性分别门善、不善、俱非——————————————————————————————三性门
四、相应门:
甲、列六位此心所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相应门
乙、受俱皆三受相应——————————————————————————————————————受俱门
遍行初遍行触等
别境次别境为欲,胜解念定慧
善善谓信惭愧,无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
烦恼烦恼为贪嗔,痴慢疑恶见
随烦恼随烦恼为忿,恨覆恼嫉悭,诳谄与害憍,无惭及无愧
掉举与昏沉、不信并懈怠、放逸及失念,散乱不正如
不定不定谓悔眠寻伺二各二
五、所依门依止根本识——————————————————————————————————所依门
六、俱转不俱转门五识随缘现,或俱或不俱,如波涛依水——————————俱转门
七、起灭分位门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
及无心二定,睡眠与闷绝——————————————————————起灭门
论文二:次中思量能变识后,应辩了境能变识相。此识差别总有六种,随六根境种类异故。谓名眼识乃至意识,随根立名具五义故。五谓依、发、属、助、如根。虽六识身皆依意转,然随不共立意识名,如五识身无相滥过。或唯依意故名意识,辩识得名,心意非例。或名色识乃至法识,随境立名顺识义故,谓于六境了别名识。
讲解:由此向下,先解释七门中的‘能变差别门’。论文曰:其次说罢第二思量能识后,应当解释第三了境能变识。这了境能变识总有六种,因为随顺六根六境不同的功能,称做: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或有问曰:识的立名,实通于根和境,为何要随根立名呢?论主答曰:因为随根立名有五种意义,例如:一者依于眼根之识,名叫眼识。二者眼根所发之识,名叫眼识。三者属于眼根之识,名叫眼识。四者帮助眼根了境之识,名叫眼识。五者识如于根名叫眼识(注:如眼根等是有情数,故眼识等也变为有情数)。眼识如此,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六识皆仗意根而发生作用,今既依根立名,就应当都叫做意识才对,何以独名第六为意识呢?答曰:虽然六识都依末那识发挥作用,但只有第六识依第七不共意根而立意之名,如前五识,各依它们不共的五根而得名,这就没有混滥不清的过失。或者说,只有第六识依于意根,所以称为意识。
问:若第六识依于意就名叫意识,那么第八识也是唯依于意;第七识,也是唯依于心,这样就应当称第八识为意识,第七识为心识才对啊!答曰:这是辩论六识之所以得名,与心意无关,不能比例。
前六识或称色识、声识、香识、味识、触识、法识,这是随境立名,与随根立名为眼识乃至意识的名义不同。所谓随境立名,就是顺著识能了别六境的意义而立识名。
论文三:色等五识唯了色等,法识通能了一切法,或能了别法,独得法识名,故六识名无相滥失。此后随境立六识名,依五色根未自在说。若得自在,诸根互用,一根发识,缘一切境,但可随根无相滥失。庄严论说:如来五根,一一皆于五境转者,且依粗显同类境说。佛地经说:成所作智,决择有情心行差别,起三业化,作四记等。若不遍缘,无此能故。然六转识所依所缘粗显极成,故此不说。前随义便,已说所依,此所缘境,义便当说。
讲解:有问曰:色等前五识所了别的色等五境,都叫做法,第六法识所了别的法境里,也有色等五境在内,何以不名色等五识为法识呢?答曰:色等五识,只能各自了别各自的境界,所以不名法识;第六识能了别一切法,所以不名色等五识而名为法识。
上面随境所立的六种识名,是依五种色根还没有得到自在位的凡夫而说的。若是得到自在位的二乘圣人,那时便能五根互用,无论用那一根发识,都能遍缘六境。因此,六识的名称只好随根而立,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以免混滥。
《大乘庄严论经》上说:如来的五根,每一根都能缘五境,但那是依粗显和同类的境界来说的。实际上,如来诸根互用,一缘一切。所以《佛地经》说:佛转五识为‘成所作智’,能够抉择各个有情的心行差别,而起身、语、意三业的对治教化。又能作一向记、分别记、反诘记、舍置记这四种记别,以决了当来的果相。如果如来不是一根遍缘诸境,怎么会有这种功能。然而六转识所依的根,所缘的境,色相粗显,这是大乘和小乘都承认的,所以本颂都略而不说。
第二章自性行相门
论文一:次言了境为性相者,双显六识自性行相。识以了境为自性故,即复用彼为行相故。由是兼释所立别名,能了别境名为识故。如契经说:眼识云何,谓依眼根了别诸色,广说乃至意识云何?谓依意根了别诸法。彼经且说不共所依未转依位见分所了,余所依了,如前已说。
讲解:第一章能变差别门,已释颂文前两句‘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现在解释第三句颂文‘了境为性相’,此句颂文是双显前六识的自性与行相。所谓双显性相,就是识以了境为它的体性,也以了境为他的行相。由此,也解释了心、意、识中‘识’的别名。因为它能了别尘境,所以名之为‘识’,简别其不同于集起的心、思量的意。例如佛经上说:眼识是如何解释呢?就是依于眼根了别一切色尘,叫做眼识。以至于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也是各依其根,各了其境;乃至意识也是依于意根,了别一切法境。经上只说六识各依其所依的根,不与余识所共,在未转识成智的凡位,是识的见分所了,至于与余识所共的:染净依、分别依、根本依,及自证分所了,在前文已讲过了。
第三章三性分别门
论文一:此六转识何性摄耶?谓善、不善、俱非性摄。俱非者谓无记,非善、不善故名俱非。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人、天乐果,虽于此世能为顺益,非于他世故不名善。能为此世、他世违损,故名不善。恶趣苦果虽于此世能为违损,非于他世,故非不善。于善、不善益损义中,不可记别,故名无记。此六转识若与信等十一相应,是善性摄。与无惭等十法相应,不善性摄。俱不相应,无记性摄。
讲解:此六转识,在三性中为那一性所摄呢?答曰:如颂文所说:‘善、不善、俱非’。俱非,就是无记。因为它既不是善,也不是不善,所以称为‘俱非’。何谓善?能于此世、他世,得到二世乐果的利益,所以名之为善。人天乐果,虽于此世能为利益,而不能于他世亦为利益,这仅是无记乐果,所以不名为善。何谓不善?能于此世、他世,得到二世苦果的损害,所以名为不善。地狱、饿鬼、畜生的恶趣苦果,虽于此世受到了苦报的损害,并非于他世亦堕恶趣,这仅是无记苦果,所以不名不善。在善的利益、或不善的损害两种意义中都无可记别的,就名叫无记。
这六转识如果和信等十一种善心所相应,那便是善性所摄。如果和无惭等十种不善法相应,那便是不善性所摄。如果善、不善都不相应,那便是无记性所摄。(注:无惭等十法:十法,是中随烦恼无惭无愧二,小随烦恼的忿、恨、恼、覆、嫉、悭、害七,及根本烦恼的嗔共为十法,此十法皆不善性摄。此外,大随烦恼八,小随烦恼的诳、谄、憍,根本烦恼的贪、痴、慢、疑、恶见,皆通不善及有覆无记摄,贪、慢不与中随烦恼同起者,全是有覆无记摄)
论文二:有义:六识三性不俱,同外门转互相违故,五识必由意识导引,俱生,同境,成善染故。若许五识三性俱行,意识尔时应通三性,便违正理,故定不俱。瑜伽等说藏识一时与转识相应三性俱起者,彼依多念。如说一心、非一生灭,无相违过。
讲解:对于六识是否与三性俱起,有两家不同的异说。第一家说:六识不能与三性同时俱起,一者六识同缘外境,而三性互违,有善即不能有恶,有恶即不能有善,善、恶不是无记,怎能同时俱起?二者前五识生起,必须由第六意识引导,才能同时俱生,同缘一境,才能成为善染。如果允许五识能够三性俱起,就应当使意识一念中也通于三性,这与正理相违,所以三性在六识里,决定不能俱起。虽然《瑜伽论》等有说:‘第八藏识,一时与转识相应,三性俱起’的话,但那是依多念而说的,并非一念俱起三性。例如说一心,并不是一念生减,所以没有三性相违的过失。
论文三:有义:六识三性容俱,率尔、等流,眼等五识,或多或少容俱起故。五识与意虽定俱生,而善性等不必同故。前所设难于此唐捐。故瑜伽说:若遇声缘从定起者,与定相应,意识俱转,余耳识生。非谓彼定相应意识能取此声。若不尔者,于此音声,不领受故,不应出定。非取声时即便出定,领受声已,若有希望,后时方出。在定耳识率尔闻声,理应非善。未转依者率尔堕心,定无记故,由此诚证五俱意识,非定与五善等性同。诸处但言五俱意识亦缘五境,不说同性。杂集论说:等引位中五识无者,依多分说。若五识中三性俱转,意随偏注,与彼性同。无偏注者便无记性。故六转识三性容俱。自在位唯善性摄,佛色、心等,道谛摄故,已永灭除戏论种故。
讲解:这是第二家护法论师的正义,他说:前六识可以三性俱起,因为率尔心是无记,而等流心有善、染,眼等五识缘境,识之生起或多或少不定,若五境当前,则五识俱起;若或一、或二、或三境当前,识就少起,这样,则眼识起率尔无记,耳识起等流善,鼻起等流不善,这不就是三性俱起了吗?因此,五识虽然和意识俱起,但他们的性质则不必相同,因此你们说六识不能与三性同时俱起,那是白说了。
所以《瑜伽论》上说︰在定中的行人,若遇声音从定中起时,他那与定相应的意识是和耳识同时俱转,并非不要耳识但凭意识就能听到声音。假若不是意识和耳识俱起,于此声音便不能领受,他如何可以出定?再者,不是在将闻声而尚未闻声时便即出定,而是在定中的耳识先已闻声,到意识有了寻求希望之后才出定的。
在定中的耳识率尔闻声,照理说这不是善法,因为在没有转识成智的凡夫位,率尔的堕心决定是无记(注:《瑜伽论》说:率尔等五心的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肯定是无记性,这是就未转依位的五识而说,转依以后只能是善性。)由此可证五俱意识虽然与五识俱起,却不一定和五识同属一性。所以很多经论但说五俱意识亦缘五境,而不说与五识同性。
虽然杂集论上说,在修等引定时定中没有五识,但那是约‘多分’而说的。所谓多分有两种情况:一者以时间论,在定中的耳识,不过是大部分时间不起,还有少部分时间是生起的。二者以五识而论,定中但有耳识,其余四识都没有。
如果五识中的三性同时俱转,五俱意识则随著偏重于某境而专注一处,其专注之境若是善色,则眼俱意识同为善性;若是恶声,则耳俱意识便同为恶性。若没有专注而兼缘五境,便是无记。所以前六转识的善、恶、无记三性,是可以同时俱起的。
以上所说,是指未得自在的凡夫位而言。如果达到解脱自在的佛位以后,则前六识纯属善性,因为佛的色、心属于无漏性的道谛所摄,此时已经永灭戏论种子了。
第四章心所相应门.泛说六位心所
论文一:六识与几心所相应?颂曰:此心所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皆三受相应。论曰:此六转识,总与六位心所相应,谓遍行等,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如属我物立我所名。心于所缘唯取总相,心所于彼亦取别相,助成心事得心所名。如画师资作模填彩。故瑜伽说:识能了别事之总相,作意了此所未了相,即诸心所所取别相。触能了此可意等相,受能了此摄受等相,想能了此言说因相,思能了此正因等相,故作意等名心所法。此表心所亦缘总相。
讲解:论主自问自答:前六识与几位心所相应呢?三十颂的颂文曰:‘此心所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皆三受相应。’意思是说:这六转识总与六位心所相应,就是遍行、别境、善、根本烦恼、随烦恼、不定。为什么这六位名叫心所呢?因为一者心所恒依心王而起,若离开心王,心所决定不生。二者心所与心王,生起同时,依于同根,缘于同境,所以他们才彼此相应。三者心所以心王为主,而系属于心王。因为有以上三义,所以名叫心所。好像属于我的东西,就说这东西是属我所有。
心所和心王的行相有何不同呢?心王在所缘的境上只取总相,不取别相;而心所则总、别兼取,来助成心王的作用,所以得心所之名。这好比作画的师父,但作画模,再由弟子依模填彩,还要考虑著色的深浅。心王和心所取境的总、别,也是这样。
所以《瑜伽论》上说:识是心王,能了别外境的总相。作意是心所,能兼了别心王所未了别的别相。触能了别外境可意、不可意等相,受能了别顺、违等相,想也能了别生起言说的因相(注:心中所想,若说出来,则想是言说之因,故称言说因相。)。思能了别业因的邪正等相,所以作意、触、受、想、思,这五法都叫做心所。这表示心所不但能缘别相,而且也兼缘总相。
论文二:余处复说欲亦能了可乐事相,胜解亦了决定事相,念亦能了串习事相,定、慧亦了得失等相。由此于境起善、染等。诸心所法皆于所缘兼取别相。
讲解:《辩中边论》上也说:欲心所也能了别可乐事相,胜解心所能了别决定事相,念心所能了别惯习事相,定、慧两个心所也能了别得失等相。由于以上这作意等十位心所,兼取外境的总相和别相,在所缘的境上生起了善十一法、烦恼二十六法、不定四法,这一切心所有法,都在所缘的境上兼取别相。
论文三:虽诸心所名义无异,而有六位种类差别,谓遍行有五,别境亦五,善有十一,烦恼有六,随烦恼有二十,不定有四,如是六位合五十一。一切心中定可得故。缘别别境而得生故,唯善心中可得生故,性是根本烦恼摄故,唯是烦恼等流性故。于善、染等皆不定故。然瑜伽论合六为五,烦恼、随烦恼皆是染故。复以四一切辩五差别,谓一切性及地、时、俱,五中遍行具四一切,别境唯有初二一切,善唯有一谓一切地,染四皆无,不定唯一,谓一切性。由此五位种类差别。
讲解:虽然一切心所在名义上没有差别,但却有不同的六位,就是遍行有五,别境有五,善有十一,烦恼有六,随烦恼有二十,不定有四。合起来总数是五十一个。
五遍行心所,与一切心(八识心王)相应,五别境心所,是缘各别境而生起,十一善心所,唯在善心中才得生起,六个根本烦恼心所,他们的体性染污能生诸惑,二十个随烦恼心所,是根本烦恼所引的等同流类,四个不定心所,它们在善、恶、无记的三性中,不一定那一性所摄。
然而《瑜伽论》上,却把六位心所合为五位,那是因为根本烦恼和随烦恼,同属染污,就把二者合而为一了。并且又以四种一切来分辨五位的差别,四一切是:一切性,指善、恶、无记三性。一切地,指三界九地。一切时,指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俱,是通于八识心王。在这四一切中,遍行心所具足四种一切,别境心所只有二种,即一切性和一切地。善心所唯有一切地,烦恼心所四种全无,不定心所唯有一切性。因此,心所才有五位种类的差别。
第五章三受门
论文一:此六转识,易脱不定,故皆容与三受相应,皆领顺、违、非二相故。领顺境相适悦身心,说名乐受。领违境相逼迫身心,说名苦受。领中庸境相于身于心,非逼非悦,名不苦乐受。如是三受或各分二,五识相应,说名身受,别依身故;意识相应,说名心受,唯依心故。又三皆通有漏、无漏,苦受亦由无漏起故。或各分三,谓见所断、修所断、非所断。又学、无学、非二,为三。或总分四:谓善、不善、有覆、无覆二无记受。有义:三受容各分四,五识俱起任运贪、痴,纯苦趣中任运烦恼不发业者,是无记故,彼皆容与苦根相应。
讲解:以上是解释颂文‘此心所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前三句,现在解释‘皆三受相应’这一句。这一句不称心所相应门,而是‘受俱门’。这六转识,因为容易间断,不定一境,所以都与三受相应,皆能领纳顺、违,或顺违俱非的三种境相。领纳顺境,使身心感觉适悦的叫做乐受;领纳违境,使身心感觉逼迫的叫做苦受;领纳顺违俱非的中庸境,对身心既非逼迫又非适悦,叫做不苦不乐的舍受。
这苦、乐、舍三受又各分为二,一者与前五识相应的,叫做五根之身受,二者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叫做心受,因为意识唯依心起。再者这三受不仅通于有漏位,也通于无漏位,因为苦受不但起于有漏,而且也由修无漏圣道的加行所生起。
这苦、乐、舍三受,又可分为两个三种:第一是约‘断’的方面来说,由分别见惑所起的是见道所断,由俱生思惑所起的是修道所断,非见思二惑所起,而通于无漏的,是非所断。第二是约‘学’的方面来说,三受通于有学、无学、非有学无学。若是断了见惑,就是有学位,若是思惑也断了,就是无学位,若是二惑都没有断,当然是‘非学’的凡夫了。
或者分为四种,就是:善心相应的三受,不善心相应的三受,有覆无记相应的三受,无覆无记相应的三受。安慧认为:三受可以各分为上述四种,因为在五识中有俱起的任运贪、痴,第六意识在纯苦趣中任运生起的烦恼,是不发业的,是无记性,它们都可以与苦根相应。
论文二:瑜伽论说:若任运生一切烦恼,皆于三受现行可得。若通一切识身者,遍与一切根相应。不通一切识身者,意地一切根相应。杂集论说:若欲界系,任运烦恼发恶行者,亦是不善。所余皆是有覆无记。故知三受各容有四。
讲解:无记通于苦受,有何为证?《瑜伽论》上说:若是任运而生起的一切烦恼————无记,它们都于三受可能现行。若是通于六识身的,那就遍六识身,都与苦、乐、舍三根相应。假如不遍通五识身,那就只有第六意识与苦、乐、舍相应了。
《阿毗达磨杂集论》说:如果欲界所系的烦恼,假定是任运烦恼能发恶行的,也是属于不善所摄。其余不发恶行,及色、无色界任运而起的烦恼,皆是有覆无记。所以知道苦、乐、舍三受,容许分为善、不善、有覆无记、无覆无记四种性别。
论文三:或总分五:谓苦、乐、忧、喜、舍。三中苦乐各分二者,逼悦身心,相各异故。由无分别,有分别故。尤重轻微有差别故。不苦不乐不分二者。非逼非悦相无异故。无分别故,平等转故。
讲解:或把三受总分为五,即苦受、乐受、忧受、喜受、舍受。三受中的苦、乐二受可各分为二种,因为所缘外境有逼迫身心和适悦身心的区别。而前五识对此并无分别,意识则有分别。五识感觉粗重,意识感觉轻微。所以逼、悦与五识相应的,名谓苦受、乐受;与意识相应的,名谓忧受、喜受。为什么不把不苦不乐的舍受,也分为二呢?因为舍受既非逼迫,又非适悦,无论在前五识或意识里,都无所分别,平等而转,所以不必再分。
论文四:诸适悦受,五识相应恒名为乐,意识相应若在欲界,初、二静虑近分,名喜,但悦心故。若在初、二静虑根本,名乐名喜,悦身心故。若在第三静虑近分根本,名乐,安静尤重无分别故。诸逼迫受,五识相应恒名为苦。
讲解:凡是适悦之受与前五识相应的,通常都叫做乐受。若是与第六识相应的,则有如下三种分别:一者在欲界,及初、二禅的近分————未到定中,名叫喜受。因为它只是悦心,而不遍悦五根。二者在初、二禅的根本定中,那不但名叫乐受,同时也叫喜受,因为它是遍悦身心。三者在第三禅,无论是近分或是根本定中,都名叫乐受。因为第三禅定的安静更加深重,没有近分和根本的分别。与前五识相应的诸逼迫受,通常都叫做苦受,因为前五识没有计度分别,所以不叫忧受。
论文五:意识俱者,有义:唯忧,逼迫心故,诸圣教说:意地戚受名忧根故。瑜伽论说:生地狱中诸有情类,异熟无间有异熟生,若忧相续。又说:地狱寻、伺忧俱,一分鬼趣,傍生亦尔。故知意地尤重戚受,尚名为忧,况余轻者?
讲解:诸逼迫受,若与前五识相应的,通常都叫做苦受。但若与意识相应,则有两家不同的异说。第一家认为:与意识相应的只是忧,以其逼迫心的缘故,因为诸圣人之教,都说意识戚受称为忧根。《瑜伽论》上也说:生于地狱中的有情,他们的异熟报果从无有间断之时,由异熟所生的前六识,前五识所受的逼迫是苦,第六识所受的逼迫是忧,如是苦、忧相续而没有休止。
《瑜伽论》又说:地狱里的有情,其寻、伺二位心所都与忧相应。一部分鬼趣和傍生趣也是如此,所以知道意识所感于地狱的最重逼迫,不称为苦而称为忧。地狱之苦尚名为忧,何况其余诸趣轻微的逼迫,自然也是忧了。
论文六:有义:通二,人、天中者恒名为忧,非尤重故。傍生、鬼界名忧名苦,杂受纯受有轻重故。捺落迦中唯名为苦,纯受尤重无分别故。瑜伽论说:若任运生一切烦恼,皆于三受现行可得,广说如前。又说:俱生萨迦耶见,唯无记性。彼边执见应知亦尔。此俱苦受非忧根摄,论说忧根非无记故。又,瑜伽说:地狱诸根余三现行定不成就,纯苦鬼界傍生亦尔。余三定是乐、喜、忧根,以彼必成现行舍故。
讲解:第二家护法论师认为:意识被逼迫时,通于忧、苦二受。在人道和天道中,通常都称忧受,因为这不是重逼。在畜生道和饿鬼道中,夹杂有喜乐的,叫做忧受;如果纯是逼迫而没有喜乐参杂在内,那就叫做苦受了。因为杂受轻,纯受重,所以才有忧、苦的分别。在捺落迦受罪处,那些地狱里的逼迫,唯名为苦,不名为忧。(注:捺落迦:梵语音译,亦称那落迦,意译不乐、可厌、苦具等;意谓地下牢狱。)同为在极严重的逼迫里,还分什么苦受忧受呢?
《瑜伽论》上说:若是任运而生的一切烦恼,都与苦、乐、舍三受相应,戚受名苦,不称为忧,已如前说。又说:第七识与生俱来的萨迦耶见(注:我见),以及执常执断的边见,都是有覆无记所摄,这二见相应的苦受,自然是苦根,不是忧根所摄。因为论上说:忧根不是无记,而是染性。《瑜伽论》上又说:地狱有情,在二十二根中,十九根现行,‘余三’的乐根、喜根、忧根只有种子,不能生起现行。因为地狱界有情只有苦受,纯苦的鬼界和畜生界也是如此。所以不起现行的三根,就是乐根、喜根、忧根。为什么呢?因为七、八二识相续不断,必定成就现行舍受。
论文七:岂不容舍,彼定不成。宁知彼文唯说容受,应不说彼定成意根。彼六容识有时无故。不应彼论唯说容受,通说意根无异因故。又若彼论依容受说,如何说彼定成八根?若谓五识不相续故,定说忧根为第八者,死生闷绝宁有忧根?有执苦根为第八者,亦同此破。设执一形为第八者,理亦不然,形不定故,彼恶业招容无形故。彼因恶业,令五根门恒受苦故,定成眼等,必有一形,于彼何用?非于无间大地狱中,可有希求淫欲事故。由斯第八定是舍根,第七、八识舍相应故。如极乐地意悦名乐无有喜根,故极苦处,意迫名苦无有忧根,故余三言定忧、喜、乐。余处说彼有等流乐,应知彼依随转理说。或彼通说余杂受处,无异熟乐名纯苦故。
讲解:前面两家诤论的重点,在《瑜伽论》上说:‘地狱定成八根,余三定不成就’这句话。第一家主张地狱定成八根,第七根是意根,第八根是忧根,余三是乐根、喜根、舍根;而第二家护法主张,第七根是苦根,第八根是舍根,余三是乐根、喜根、忧根。舍根在‘定成八根’之列。
这时第一家诘难曰:地狱有情完全是不可意境,那里容有舍受呢?并且论上说,‘余三’不成就,你怎知道不是舍受不成就,而是乐、喜、忧三受不成就呢?所以第一家要在余三中去掉舍受,加上忧受。
护法论师回答:你怎么知道‘余三定不成就’就是舍受呢?如果是舍受的话,就应当不说定成意根啊。因为意根的建立,一则与舍受相应,二则能生意识。现在舍受既不成就,六转识又有时间断。可见意根不能成就,意根既不能成就,那第七识还是苦根。第七识既是苦根,那第八识当然是舍根而不是忧根了。《瑜伽论》上说‘余三不成就’,其中不成就说的就是舍受。如果认为因为五识不相续,所以一定要说忧根为第八根。在死生闷绝时怎么会有忧根呢?
有一种人执苦根为第八根,此不应理,亦同此破。倘若执于男女二形的淫根,成就一形为第八根者,理亦不然,因为形是不一定的,由恶业招感的地狱罪报,也可能是无形的。地狱众生既由恶业之故,使五根不断受苦,才成就了眼等五根,试问他要男根何用?总不能说在无间大地狱中,还希望做出淫欲的行为。基于以上理由,那第八决定是舍根了。因为恒转的第七、八二识,是与舍受相应的。例如第三禅定的极乐地,只有意识所感的适悦名叫乐受,而没有喜根。所以地狱的极苦处,也只有意识所感的逼迫名叫苦受,而没有忧根。因此,那所谓‘余三不成就’,决定是忧、喜、乐三受,而不是舍受。
那么,何以《摄论》上说:苦处也有等流之乐呢?须知这是随顺小乘转说,或者是通说其余的鬼、畜二趣,他们虽在受苦,间或也有少分等流乐受。所以叫做其余的杂受处。在无间地狱里毫无异熟乐之可言,全是纯苦之受。
论文八:然诸圣教,意地戚受名忧根者,依多分说,或随转门,无相违过。瑜伽论说:生地狱中诸有情类,异熟无间有异熟生苦忧相续。又说,地狱寻、伺、忧俱,一分鬼趣,傍生亦尔者,亦依随转门。又彼苦根意识俱者,是余忧类,假说为忧。或彼苦根损身心故,虽苦根摄,而亦名忧。如近分喜,益身心故,虽是喜根而亦名乐。显扬论等具显此义。然未至地定无乐根,彼说唯有十一根故。由此应知意地戚受,纯受苦处亦苦根摄。此等圣教差别多门。恐文增广故不繁述。
讲解:然而有经论上说:与意识相应的戚受叫做忧根。但那不是单约地狱来论,而是依人、天趣的全部,和鬼、畜趣的一部分而说的,或者是随顺小乘有部而说的,这和《瑜伽论》并不矛盾。《瑜珈论》上说:‘生在地狱里的有情,他们的异熟识没有间断;有异熟所生的前六识,五识所受的是苦;意识所受的是忧,就这样苦、忧相续。’又说:‘地狱有情,他们与意识相应的寻、伺二法,也与忧根相应。’不但地狱,就是一部分鬼趣和畜生也是这样,这也是随转小乘有部教理所说的方便法门。再者,地狱苦根与意识相应的,也同其余人、天等杂受处的忧根相似,虽亦假说为忧,宝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忧受,而是假说为忧。地狱苦根能损害有情身心,虽属苦根所摄,但也可称为忧受。就像在初、二禅天未到根本定的近分定时,身心感到喜悦的顺益,虽是喜根,也可称为乐受。在《显扬论》等都有所显示此义。由此应知,意地戚楚之受,在纯粹受苦的处所也属于苦根。像这样的圣人教诲,差别是多方面的,如三受、五受、有报、无报、界地系、何地断等,涉及广泛,不再细述。
论文九:有义,六识三受不俱,皆外门转,互相违故。五俱意识同五所缘,五三受俱,意亦应尔,便违正理,故必不俱。瑜伽等说:藏识一时与转识相应,三受俱起者,彼依多念,如说一心非一生灭,无相违过。
讲解:这是两家在六识与三受俱不俱起上所起的诤论。第一家说:六识与三受是不能俱起的。因为六识都是向外缘境,而三受则是互相违背的。因为五俱意识与五识俱缘现境时,五识与三受相应,当然也与意识相应。这样一念有苦、乐、舍三受,便与六识同缘的正理相违背。所以六识与三受必不俱转。虽然《瑜伽》、《显扬》等论上说:第八藏识一时与前六识相应,三受俱起,但那是依多念而言,并不是一念俱起三受。如说一心,并不表示一念生灭,所以没有三受相违的过失。
论文十:有义:六识三受容俱,顺、违、中境,容俱受故。意不定与五受同故。于偏注境起一受故,无偏注者便起舍故。由斯六识三受容俱。得自在位唯乐、喜、舍,诸佛已断忧苦事故。
讲解:第二家护法认为:六识与三受是可以俱起的,它可以接受顺境、违境、顺违俱非的中庸境。但意识不一定与五识的三受相同。当意识与五识同缘五境时,那意识若专注于顺境,便生起乐受;若专注于违境,便生起苦受,若无偏重的顺、违之境可资专注,那便生起舍受。所以六识可以与三受相应俱起。以上是指未得自在的有漏位而言,若得自在位后,那就只有乐受、喜受、舍受相应,因为诸佛已经断了忧、苦之因。
第六章心所相应门.详释六位心所
第一节遍行.别境心所
论文一:前所略标六位心所,今应广显彼差别相。且初二位其相云何?颂曰:初遍行触等,次别境谓欲,胜解念定慧,所缘事不同。
讲解:这是次举六颂的第二颂。前面已经略把六位心所标明,现在再详细解释六位心所的差别。问曰:这六位心所的前二位,他们的义相是怎么样呢?颂文答曰:‘初遍行触等,次别境谓欲,胜解念定慧,所缘事不同。’
论文二:论曰:六位中初遍行心所即触等五,如前广说。此遍行相云何应知?由教及理为定量故。此中教者,如契经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三和合触,与触俱生有受、想、思。乃至广说,由斯触等四是遍行。又契经说:若根不坏,境界现前,作意正起,方能生识。余经复言:若复于此作意,即于此了别,若于此了别,即于此作意。是故此二恒共和合。乃至广说,由此作意亦是遍行。此等圣教诚证不一。
讲解:颂文第一句‘初遍行触等’,是说六位中的遍行心所有五,就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遍行心所,在前面解释初能变中已经说过。然而这五个遍行的义相是什么呢?我们由圣教和正理来做认定的标准。圣教的经上说:‘以眼根为增上缘,色境为所缘缘,便能生起眼识。根、境、识三法和合便能生触。与触同时生起的有受、想、思。乃至广泛的说,以法为缘而生意识。所以知道这触、受、想、思四法是遍行心所。《象迹喻经》上说:倘若眼根没有坏,又有境界现前,而且作意生起,然后才能生识。《起尽经》上说:在这个境上生起作意,就在这个境生起了别;在这个境生起了别,也就在这个境上生起作意。因此,这作意与了别二法时常和合一处。由此可知作意心所也是遍行心所法之一。像这样的圣教很多,不止一经。
论文三:理谓识起必有三和,彼定生触,必由触有。若无触者,心、心所法应不和合触一境故。作意引心令趣自境,此若无者,心应无故。受能领纳顺、违、中境,令心等起欢、戚、舍相,无心起时,无随一故。想能安立自境分齐,若心起时无此想者,应不能取境分齐相。思令心取正因等相,造作善等,无心起位无此随一,故必有思。由此证知触等五法心起必有,故是遍行。余非遍行,义至当说。
讲解:前面是引教为证,现在是从理论上说。诸识生起,必定依根缘境,根、境、识三法和合,必定生触。反之三法和合,也必定因触而有。倘若没有触,心、心所法就不能和合起来共触一境,所以肯定触是遍行心所。
作意心所的功能,是引导心王使他趣向于自心所缘的外境。作意若无,心王就不能生起。受能领纳适意的顺境、不适意的违境、顺违俱非的中庸境,使心随境生起乐、苦、舍相,这三相就叫做‘三受’。想的功能,是在自心所取的境上,安立了或青、或黄,或多、或少,或大、小等差别相。当心生起时,假使没有想心所,就不能取境界的分别相。还有思心所,他能令心取正、邪等业因,来造作善、恶、无记等业。在没有心识生起时,就没有这个思心所随之而起。但有心识生起,必有此思。由于以上道理的证明,我们知道这遍行五心所,心起必有,故称遍行。余非遍行,下文当说。
论文四:次别境者,谓欲至慧,所缘境事多分不同,故六位中次初说故。云所为欲,于所乐境希望为性,勤依为业。有义:所乐谓可欣境,于可欣事欲见、闻等有希望故。于所厌事希彼不合,望彼别离,岂非有欲?此但求彼不合离时,可欣自体,非可厌事,故于可厌及中容境一向无欲。缘可欣事若不希望,亦无欲起。
讲解:其次讲颂文的后三句:‘次别境谓欲,胜解念定慧,所缘事不同。’什么叫做‘欲’呢?就是对于所乐的境界生起希望,这是其体性;辛勤的追求,就是其业用。于此,有三家不同的异说。第一家说:所乐的定义,就是可欣的境界。对于可欣的境界,有欲见、欲闻、欲觉、欲知的希望,这就是欲。有问曰:对于讨厌的事未遇合的,希望不要遇合;既遇合的,希望早点离开,这岂不也是欲吗?论主答曰:这不过是希望不合,人们只追求可欣的外境,并不追求可厌的外境。因为对于可厌境和中庸境,不生希望,也没有欲心生起。
论文五:有义:所乐,谓所求境,于可欣厌求合离等有希望故。于中庸境一向无欲,缘欣厌事若不希求亦无欲起。有义:所乐谓欲观境,于一切事欲观察者,有希望故。若不欲观,随因境势任运缘者,即全无欲,由斯理趣,欲非遍行。有说,要由希望境力,诸心、心所方取所缘,故经说欲为诸法本。
讲解:第二家的解释是:所乐者就是所求境,对于可欣的事未合求合,既合求不离;对于可厌的事,未合求不合,既合求离。因为有此希望,所以才叫做欲。对于中庸境一向无欲。对于所缘可欣、可厌之境,若无合、离的希求,也不会有欲心所生起。
第三家则说:所乐就是欲观境,对一切想观察的事物就有希望,这个观察的希望就是欲。如果你不想观察,只是随著境界的力任运而缘,那就不管他是好是坏,都不会有欲心所生起。由于这个道理,所以欲心所但属别境,而不属遍行。小乘有部说:因为有希望缘取外境之力,那一切心、心所才能取境,所以经上说欲是一切法的根本。
论文六:彼说不然,心等取境由作意故,诸圣教说:作意现前能生识故,曾无处说,由欲能生心、心所故。如说诸法爱为根本,岂心、心所皆由爱生?故说欲为诸法本者,说欲所起一切事业,或说善欲能发正勤,由彼助成一切善事,故论说此勤依为业。
讲解:论主答曰:这种说法不对,心、心所之缘取外境是由于作意,并不是欲。很多的经论上说:作意现前能够生识,没有一处说由欲而生起心、心所法。例如有说诸法以爱为本,难道说心、心所都是由爱而起吗?以此例知,所谓‘欲为诸法根本’的话,那是说,由欲所起的一切行为,都是以欲为根本的。或说善法的欲,能发正勤,复由正勤来助成欲的一切善事。所以《显扬圣教论》上说:欲是生起正勤的动力。
论文七:云何胜解?于决定境印持为性,不可引转为业。谓邪正等教理证力,于所取境审决印持,由此异缘不能引转。故犹豫境胜解全无,非审决心亦无胜解,由斯胜解非遍行摄。有说:心等取自境时无拘碍故,皆有胜解。彼说非理,所以者何?能不碍者即诸法故,所不碍者即心等故。胜发起者根作意故,若由此故彼胜发起,此应复待余,便有无穷失。
讲解:什么叫做胜解呢?就是对于外境的判断,一经决定,即不可引转。意思是说:对于邪教、邪理,或正教、正理,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后,纵然再遇异缘,也不能使他改变既定的决心。因此,犹豫不决的境界没有胜解,不是审决之心也没有胜解。由此可见,胜解心所但属别境,而不是遍行。
说一切有部认为:只要心、心所缘取自心所缘的外境时,没有东西从中阻碍,都有胜解,何待审决印持?论主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合理,因为能不阻碍的,是所缘的一切法,不是胜解;所不阻碍的,是心、心所法本身,也不是胜解。怎么以不碍为胜解呢?若说不碍的心、心所,由胜解的增上胜缘所发起,那也不对,那是根和作意二法,与胜解无关。若说胜解的增上之力,根和作意才能发起,那这胜解也应当更待余法来做他的增上缘,这样的缘复待缘,岂非有无穷的过失吗?
论文八:云何为念,于曾习境令心明记不忘为性,定依为业。谓数忆持曾所受境令不忘失,能引定故。于曾未受体类境中全不起念。设曾所受不能明记念亦不生。故念必非遍行所摄。有说:心起,必与念俱,能为后时忆念因故。彼说非理,勿于后时,有痴、信等。前亦有故。前心、心所或想势力,足为后时忆念因故。
讲解:什么叫做念?对于曾经熏习过的境界,令心明白记忆而不忘失,是禅定所依的基础。意思就是说,数数忆持,不断专注于曾经领受过的境界,令心不忘,能引生定。例如专念曾经闻受的正法,能令一心不乱,便是引定。对于未曾经受的事物不会起任何忆念。对于曾经闻受之境而不能明记不忘,则‘念’也不会生起。所以念心所但属别境,而不属于遍行。
说一切有部认为:‘凡是心生起的时候,必定与念心所同起,能做为后来忆念的原因。’论主驳曰:这样说法不合理,不可说后面有痴、信等,从前也有,就是遍行,如果这样说,那痴但属染;信但属善,他如何能是遍行?再者,前心、心所取境熏习的功能,或凭想像明记的势力,已经足够为后时忆念之因,就不需要前念了。
论文九:云何为定?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谓观得、失、俱非境中,由定令心专注不散,依斯便有决择智生。心专注言显所欲住即便能住,非唯一境。不尔,见道历观诸谛,前后境别应无等持。若不系心,专注于境,便无定起,故非遍行。有说:尔时亦有定起,但相微隐,应说诚言。若定能令心等和合,同趣一境,故是遍行。理亦不然,是触用故。若谓此定令刹那顷心不易缘,故遍行摄。亦不应理,一刹那心,自于所缘无易义故。若言由定心取所缘故遍行摄,彼亦非理,作意令心取所缘故。有说:此定体即是心。经说为心学,心一境性故。彼非诚证,依定摄心,令心一境,说彼言故。根、力、觉支、道支等摄。如念、慧等非即心故。
讲解:什么叫做定呢?在所观的外境上,令心专注而不散乱,智慧依此而生。也就是说,在观察或得、或失,或得失俱非的境中,由此定令心专注而不散乱。依此便有决择的无漏智慧生起。所谓‘心专注’的话,是显示心所欲住于此,便能安住,并不是前后唯缘一境。否则,见道位中以十六心观各个真理时,前后之境就有区别,就不会有平等持心的三昧定了。若以散心别缘,而不系心专注于转深境位,便不会有禅定生起。所以定心所但属别境,而不是遍行。
正理师认为:心不专注时也有定生起,不过他的行相微隐难知。谕主破他说:解释法义应说诚实语,如果说定能使心、心所和合同缘一境,所以也是遍行,这理由不对,和合是触的作用,与定无关。若说此定能令一刹那顷的心住于一境,不改易所缘,就是遍行所摄,也不合理,因为一刹那的心自能对于所缘的境没有改易,也不必有定。如果说由定才能令心取境,所以他是遍行所摄,也不合理,因为令心取境的是作意的功能,不是定的作用。
又有经量部师说:这个定的自体就是心,不是另外有体。因为经上说三学中定是心学,令心一境为性。论主破斥说:心学是说定依摄于心,使心专注一境,所以称为心。并不是其体就是心。定是五根中的定根,五力中的定力,七觉支中的定觉支,八圣道中的正定分所摄,就像别境中的念、慧等心所一样,各有各体,并非定就是心。
论文十:云何为慧?于所观境简择为性,断疑为业。谓观得、失、俱非境中,由慧推求得决定故。于非观境愚昧心中无简择故,非遍行摄。有说:尔时亦有慧起,但相微隐。天爱宁知?对法说为大地法故。诸部对法,展转相违,汝等如何执为定量。唯触等五经说遍行,说十非经,不应固执。然欲等五非触等故,定非遍行,如信、贪等。
讲解:什么叫做慧呢?在所观察的境上,简别决择为性;断绝疑惑为业。对于所经受或得、或失,或得失俱非的尘境中,由慧推求,而得决定无疑。在非所观境、及愚昧心中,就没有简择的智慧。所以慧心所但属别境,不是遍行所摄。
有部师说:在非所观境及愚昧心中也有慧起,不过他的行相微细隐伏,如微细物为大器盛受,不易显知。不过对法论上说:慧心所为十大地法之一,而小乘的大地法即相当于大乘的遍行。(注:大地法:俱舍论颂云:受想思触欲,慧念与作意,胜解三摩地,遍于一切心。此十皆名大地法)
论主破曰:小乘诸部对法,如发智论、六足论等,展转差别相违,你们如何拿它作为定量?只有触、作意、受、想、思五法,经上说是遍行;至于有十个遍行的话,那不是经上所说。这欲、胜解、念、定、慧五法,与触等不同,别境所摄,一定不是遍行,例如善法的信等,烦恼法的贪等,属性不同。
论文十一:有义:此五定互相资。随一起时必有余四。有义:不定。瑜伽说:此四一切中无后二故。又说:此五缘四境生,所缘能缘非定俱故。应说:此五或时起一,谓于所乐唯起希望,或于决定唯起印解,或于曾习唯起忆念,或于所观唯起专注。谓愚昧类为止散心,虽专注所缘,而不能简择。世共知彼有定无慧。
讲解:此下讲欲等五法是否俱起,此有两家相反的说法。第一家说:这欲、胜解、念、定、慧五法,决定互相资助,有一法起时,其余的四法必定与之同起。第二家说:不然,因为《瑜伽论》上说:这五个心所,在四一切中(注:一切性、一切地、一切时、一切俱)没有后面一切时、一切俱两个一切。论上又说:这五个心所,是缘四种境界而生的,欲缘所乐境,胜解缘决定境,念缘曾习境,定、慧缘所观境。这所缘的四种境界,及能缘的五个心所,他们不可能同时俱起。
这五个心所,对境一次只起一个,就是或在所乐境上,唯起希望的欲;或在决定境上,唯起印持的胜解;或在曾习境上,唯起不忘的念;或在所观境上,但起专注的定。愚昧的人为了摄敛粗动散心,虽然专注于所缘之境,但不能对此进行鉴别和判断,所以世间共知他们有定无慧。
论文十二:彼加行位,少有闻思,故说等持缘所观境,或依多分,故说是言,如戏忘天专注一境,起贪、嗔等,有定无慧,诸如是等,其类实繁。或于所观,唯起简择。谓不专注,驰散推求。
讲述:那些愚昧的人,在定前的加行位时,也有一点闻教于师,思维于己的闻、思二慧,所以说定所缘境,也叫做所观境。或者依所观之境,除少数人是有定无慧外,大部分的行者是定、慧俱起,所以就依此来说,这定境名为所观。例如欲界戏忘天人,他们亦专注于游乐一境,忘失正念,起了贪、嗔等烦恼,所以说他们于所观境有定无慧。像这样有定无慧的情况实在很多。或者是在所观境上,唯起简择之慧,谓掉举多者不能专注一境,唯务驰散推求法相或义理,所以有慧无定。
论文十三:或时起二,谓于所乐、决定境中,起欲、胜解。或于所乐、曾习境中起欲及念。如是乃至于所观境起定及慧,合有十二。或时起三,谓于所乐、决定、曾习,起欲、解、念,如是乃至于曾习、所观起念、定、慧,合有十三。或时起四,谓于所乐、决定、曾习、所观境中起前四种,如是乃至于决定、曾习、所观境中起后四种,合有五四。或时起五,谓于所乐、决定、曾习、所观境中,俱起五种。如是于四起欲等五,总别合有三十一句。或有心位五皆不起,如非四境、率尔堕心及藏识俱,此类非一。
讲述:有时对境一次,生起两种心所,如一者于所乐、决定境中,生起欲和胜解。二者于所乐、曾习境中,生起欲和念。三者于所乐及所观境中,生起欲和定。四者于所乐及所观境中,生起欲和慧。五者对决定及曾习境,生起胜解和念。六者对决定及所观境,生起胜解和定。七者对决定及所观境,生起胜解和慧。八者对曾习及所观境,生起念和定。九者对曾习及所观境,生起念和慧。十者对所观境,生起定及慧,合有十个二。
有时对境一次,生起三个心所,合十次生起的心所,总共有十个三。如于所乐、决定、曾习三境中,生起欲、胜解、念。于所乐、决定、所观三境中,生起欲、胜解、定。余略。有时对境一次,生起四个心所,合五次所起的心所,有五个四。如于所乐、决定、曾习、所观境中,生起欲、胜解、念、定。于所乐、决定、曾习、所观境中,生起欲、胜解、念、慧。有时对境一次,生起五个心所,这当然是于所乐、决定、曾习、所观境中,生起欲、胜解、念、定、慧五个心所。
综上所述,一次起一个心所的有五次,一次起两个心所的有十次,一次起三个心所的也有十次,一次起四个心所的有五次,一次起五个心所的有一次。这样连一次的‘总’及三十次的‘别’,一共三十一次。但这欲、胜解,念、定、慧五个心所,莫说在无心位,就是在有心位,也有全部不起的时侯。如果不是所乐、决定、曾习、所观的四境现前,而是率尔心所起的六识,及与藏识相应的心所,都没有它们。这一类说法很多,非止一类。
论文十四:第七、八识,此别境五,随位有无,如前已说。第六意识诸位容俱,依转未转皆不遮故。有义:五识此五皆无。缘已得境无希望故,不能审决无印持故。恒取新境无追忆故,自性散动无专注故,不能推度无简择故。
讲解:第七、八二识与五位别境,随位或有或无,前面已说。至于第六意识,在未转依位,或五法俱起,或一一别起;若在已转依位,那是全部都有的。因为无论转依的无漏,或未转依的有漏,都没有遮简。若在前五识,则有两家异说。第一家说:前五识里没有别境五心所,因为它只缘已得之境,不缘未得之境,所以没有希望的欲;它不能审虑作出决定,所以没有胜解。它永远缘取新境,不缘过去,所以没有追忆的念。它自性散动,不能专注一境,所以没有定。它不能推求和量度,所以也没有简择的慧。
论文十五:有义:五识容有此五,虽无于境增上希望,而有微劣乐境义故。于境虽无增上审决,而有微劣印境义故。虽无明记曾习境体,而有微劣念境类故。虽不作意系念一境,而有微劣专注义故。遮等引故,说性散动,非遮等持故容有定。虽于所缘不能推度,而有微劣简择义故。由此圣教说眼、耳通,是眼、耳识相应智性。余三准此有慧无失。未自在位此五或无,得自在时此五定有。乐观诸境欲无减故,印境胜解常无减故,忆习增受念无减故,又佛五识缘三世故,如来无有不定心故,五识皆有作事智故。
讲解:第二家说,前五识里,容或俱有这别境五法。因为前五识的缘境,虽然没有强烈的希望,但在第六识的导引下,对于乐境也有微劣的希望,所以有欲。虽然没有强盛的审决判断,但也有微劣印境的意义,所以有胜解。虽然不能明记曾经历境界,但也有微劣对现境的忆念,所以有念。虽然没有作意加行系念一境,但也有微劣专注的意义。因为其不能有等引之定,所以说它‘自性散动’,但不能否认有它有等持之定,所以容许有定。前五识虽然对于所缘外境不能推理,但有微弱的鉴别意义,所以《瑜伽师地论》上说:眼通与耳通,是与眼、耳二识相应的智慧。既然眼、耳二识有慧,所以其余的鼻、舌、身三识,与前二识一样,也有智慧,此说并无过失。
在没有得到自在的凡位,这五种别境或许没有,但在自在解脱位,这五种别境则决定都有。因为自在圣位的五识,于乐观境的欲,印持境的胜解,忆习曾受境的念,都没有减损。再者,佛地的五识,能缘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心没有不定的时候。佛地的五识已经转为成所作智,又岂能无慧。(注:等持,定的别名,意谓平等持心,心住一境,平等维持。)
论文十六:此别境五,何受相应?有义:欲三,除忧、苦受,以彼二境非所乐故。余四通四,唯除苦受,以审决等五识无故。
讲解:这五个别境心所,与喜、乐、忧、苦、舍五受的何受相应呢?此有两家不同的说法。第一家说:除了忧、苦二受,欲心所和喜、乐、舍三受相应。因为忧、苦二受不是欲的所乐境。其余的胜解、念、定、慧四心所,则通于五受之四,唯除去苦受。因为与苦受相应的五识里,没有这胜解、念、定、慧的四个心所。
论文十七:有义:一切五受相应。论说忧根于无上法,思慕愁戚求欲证故,纯受苦处希求解脱,意有苦根,前已说故。论说贪爱,忧苦相应,此贪爱俱必有欲故,苦根既有意识相应,审决等四苦俱何咎?又五识俱,亦有微细印境等四,义如前说。由斯欲等,五受相应。此五复依性、界、学等,诸门分别。如理应思。
讲解:第二家说:五个别境都与五受相应。因为《瑜伽师地论》说:忧根对于无上妙法思慕愁戚,希望得证,是欲与忧相应之证。纯受苦处的地狱、鬼、畜,他们那希求解脱的意识里,也有苦根,前面已经说过。所以欲心所,也与苦受相应。论上还说,贪爱与忧、苦相应,此贪爱俱起时,必定有欲,这就是欲心所与忧、苦并俱之证。苦根既与意识相应,那其余与意识相应的胜解、念、定、慧四法,也可与苦受相应,有何过咎?
再者,五识与意识俱起时,亦有微细印持境的胜解,曾习境的念,所观境的定、慧四法,其义已如前面所说。因此别境五法,都与五受相应。
这五个别境,和有心必起的五遍行不同,所以在别境五法后,复依三性、三界、三学等诸门加以分别。例如:四一切的一切性,就是三性的分别;一切地,就是三界的分别;转依、未转依,就是依断见、思二惑的无学、未断思惑的有学、二惑未断的非学无学,这三学的分别,应该如理思索。
第二节善心所
论文一:已说遍行、别境二位,善位心所其相云何?颂曰:善谓信惭愧,无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论曰:唯善心俱名善心所,谓信、惭等,定有十一。云何为信?于实德能,深忍乐欲,心净为性,对治不信,乐善为业。然信差别,略有三种:一信实有,谓于诸法实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谓于三宝真净德中深信乐故。三信有能,谓于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由斯对治不信彼心。爱乐证修世出世善。
讲解:这是次举六颂的第三颂。前面已说遍行、别境二位,至于第三位的善心所,其义相是怎么样呢?颂文说:善心所十一个,是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勤、轻安、不放逸、行舍、不害。分别解释如下。
长行解释颂文曰:所谓善心所,是唯独与善心俱起的心所,才能叫做善心所。善心所决定只有十一个。什么叫做信呢?对于实、德、能诸法,深能忍可欲乐,以心清净为性,以对治不信,好乐善法为其业用。然而信的差别有三种:第一是信实有体性之法,对于佛陀所说的世出世间诸法,实有其事,实有正理中的正因正果,深信不疑。第二是信有德,对于佛、法、僧三宝的真净功德,深信而喜乐。第三种是信有能,对于一切世、出世间之善法,深信其有势力,能得乐果,能成圣道,生起希望愿欲。由此三信,能够对治不信此三之心,以好乐而修证世、出世间的一切善法。
论文二:忍谓胜解,此即信因。乐欲谓欲,即是信果。确陈此信自相是何?岂不适言心净为性?此犹未了彼心净言。若净即心,应非心所,若令心净惭等何别?心俱净法为难亦然。此性澄清能净心等,以心胜故立心净名,如水清珠能清浊水。惭等虽善,非净为相,此净为相,无滥彼失。又诸染法各别有相,唯有不信自相浑浊,复能浑浊余心、心所,如极秽物自秽秽他,信正翻彼,故净为相。
讲解:外人问曰: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已经知道忍可的意义,就是胜解;也就是能生信的因。乐欲,就是欲心所,也就是信所生的果。那么,更应当确实指陈,这信的自相是什么?论主答曰:适才已说过,心净就是信的特性。
外人诘难说:你还没有讲清楚‘心净’的意思,如果‘净就是心’,这是持业释,信就不应当是心所法。如果‘心净’是使心清净,这就是依主释,这与惭等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心净’是指心与净法相俱,此为邻近释,其诘难同上所述。
论主解释说:这信的体性湛然澄清,能令其余的心、心所法清净。因为心王是主,所以但说心净,实际上亦包括心所。就像水清珠投入浊水,能使浊水清净一样。惭等体性是善,而他们的自相并非能净,不过是所净而已。唯有这信心所是以能净为自相。所以信和惭等并没有相滥的过失。
再者,一切染法各有各的自相,唯有大随烦恼里的‘不信’,它不但自相浑浊,并且能令其余的心、心所法也和它一样浑浊。好像一个极其污秽的东西,不但自己污秽,而且也染污了其他的东西。信和浑浊的不信相反,所以信以净为特性。
论文三:有说:信者爱乐为相。应通三性,体应即欲,又应苦集非信所缘。有执信者随顺为相。应通三性,即胜解欲。若印顺者即胜解故,若乐顺者即是欲故。离彼二体无顺相故,由此应知心净是信。
讲解:有人说:信是以爱乐为其特性。如果照这样说,那信就应当不但是善,而是遍通善、恶、无记三性了。因为爱乐是‘欲’所缘之境,而‘欲’是通于三性的。再者,苦、集、灭、道四谛,都是信的所缘境,如果以爱乐为信,那苦、集二谛就不是信的所缘境了。那有圣者爱乐苦、集之理?
又有诘难曰:信是以随顺为其特性。论主难曰:不然,境有三性,当然随顺亦通三性。果然如此,则随顺就成了胜解或欲,而不是信心所了。诘难者转救曰:虽然说随顺,本体并非胜解或欲。论主反难:不然,如果认定随顺,便是胜解,如果是所乐的随顺,便是欲。那么离开胜解、欲两个心所,便没有随顺的自相可言了。由此应知,所谓爱乐、随顺,都不是信的自相,心净才是信的自相。
论文四:云何为惭?依自法力,崇重贤、善为性,对治无惭,止息恶行为业。谓依自法尊贵增上,崇重贤、善,羞耻过恶,对治无惭,息诸恶行。
讲解:什么叫做惭?依靠自己之力和所理解的法,崇敬有贤德的人;对于一切有漏、无漏的善法皆生崇重,对治无惭,止息恶行。换句话说:就是依靠自身的自尊自重之力,去崇贤重善,以自己所犯的过恶感到羞耻,对治无惭,止息一切非法的恶行。
论文五:云何为愧?依世间力,轻拒暴恶为性,对治无愧,止息恶行为业。谓依世间诃厌增上,轻拒暴恶羞耻过罪,对治无愧,息诸恶业。
讲解:什么叫做愧?依于世间舆论的力量,对于暴恶的事拒而不作。愧的业用是对治无愧,止息恶行。也就是说:依于世人的诃责,和自己对于暴行的厌恶,以此二种增上缘力,拒与暴恶之人为伍,拒作暴恶之事,以对治无愧,止息一切非法的恶行。
论文六:羞耻过恶,是二通相,故诸圣教假说为体。若执羞耻为二别相,应惭与愧体无差别。则此二法定不相应。非受、想等有此义故。若待自他立二别者,应非实有,便违圣教。若许惭、愧实而别起,复违论说十遍善心。
讲解:对于自己所犯的过恶感到羞耻,是惭、愧共同的特性。所以诸圣教都依此共同特性,假说惭、愧二法别体。如果执著于羞耻是惭、愧二法的别相,则惭也是羞耻,愧也是羞耻,惭、愧二法就没有差别了。既没有差别,那就是一体。如是一体,则二法就不能相应同起。例如受、想等遍行五法各别有体,那才能相应,并不是一体相应。如果你们对自法是惭,对世间是愧,这样建立了二个别体,那也不对。因为二法既是待缘而成,那就应当不是实有。然而说不实有,又违背了经典的道理。如果许惭、愧实有而又各别而起,那又违背《瑜伽论》所说:十一种善法除了轻安之外,其余的十种都是遍一切善心,可见不是各别而起。
论文七:崇重轻拒,若二别者,所缘有异应不俱生。二失既同,何乃偏责。谁言二法所缘有异?不尔、如何?善心起时随缘何境,皆崇重善及轻拒恶义。故惭与愧俱遍善心,所缘无别。岂不我说亦有此义?汝执惭愧自相既同,何理能遮前所设难?然圣教说顾自他者,自法名自,世间名他。或即此中崇拒善恶,于己损、益,名自他故。
讲解:外人又问:惭是崇重善法,愧是轻拒恶法,以此建立二种别相。所以所缘的境既不相同,那惭、愧二法应当不能俱起。这和不俱、别起的两种过失相同,为什么偏要责难我们?论主回答:谁说惭、愧二法所缘的境有不同呢?外人难曰:不是不同是什么?论主解释:当善心生起的时候,随便缘什么境,都有崇重善法,轻拒恶法的意义,这是惭和愧的二种别相。别相就是不同的功用,惭的功用是崇善,愧的功用是拒恶。
外人称:照你这样说,岂不和我前面所说一样吗?论主回答:你既然认为惭、愧二法自相相同,你有什么理由可以遮除我前面所设疑难?然而经论对自、他二别的解释是:自立的法叫做自,世间的法叫做他。或者就是上面说的:崇重有益于己的善法叫做‘自’;轻拒有损于己的恶法叫做‘他’。
论文八:无贪等者,等无嗔、痴。此三名根,生善胜故,三不善根近对治故。云何无贪?于有、有具,无著为性,对治贪著,作善为业。
讲解:以上合解惭、愧,此下解释颂文的‘无贪等三根’,等者就是连无嗔、无痴都包括在内。这无贪、无嗔、无痴三心所,为什么称为三善根?根者能生义,有能生善法的殊胜功用。又能各别对治三不善根贪、嗔、痴。什么叫做无贪?对于三界和造成三界轮回的条件皆无贪著,这是它的特性,对治贪著,令人行善,这是它的作用。‘于有、有具无著为性’,有是三有,亦即是三界,这是有情的依报。有具是生于三界之因,即惑与业。对三界不生耽著,是无贪的特性。对治贪著,止恶作善,是无贪的业用。
论文九:云何无嗔?于苦、苦具,无恚为性,对治嗔恚,作善为业。善心起时,随缘何境皆于有等无著无恚。观有等立非要缘彼,如前惭愧观善恶立,故此二种俱遍善心。
讲解:什么叫做无嗔?逆境当前不生恚恨之心叫无嗔。‘于苦、苦具无恚为性’,苦是三界苦果,即苦苦、坏苦、行苦,苦具是苦果生成之因。对于苦因苦果不起嗔恚,是无嗔的特性;对治嗔恚,止恶作善,是无嗔的业用。有问:无贪缘乐境,无嗔缘苦境,它们缘境有异,怎能同时生起?既不能同时生起,何以能遍一切善心?论主答:当善心起时,随便缘什么境都有它们生起。对于三界的乐境不起贪著,对于三界的苦境不起嗔恨,这是依观待苦乐而建立的。所以无贪、无嗔二法,是俱时而起,遍一切善心。
论文十:云何无痴,于诸理事明解为性,对治愚痴,作善为业。有义:无痴,即慧为性。集论说此:报、教、证、智,决择为体。生得闻、思、修所生慧,如次皆是决择性故。此虽即慧,为显善品有胜功能,如烦恼见,故复别说。有义:无痴,非即是慧,别有自性正对无明。如无贪、嗔善根摄故。论说大悲,无嗔、痴摄,非根摄故。若彼无痴,以慧为性,大悲如力等应慧等根摄。又若无痴无别自性,如不害等应非实物。便违论说十一善中三世俗有,余皆是实。然集论说慧为体者,举彼因果显此自性,如以忍乐表信自体,理必应尔。以贪、嗔、痴六识相应,正烦恼摄,起恶胜故,立不善根。断彼必由通、别对治。通唯善慧,别即三根,由此无痴必应别有。
讲解:什么叫做无痴?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明确理解而不迷惑,即为其特性;能够对治愚痴,令人止恶为善,即为其业用。如要细释,则有两家不同主张。第一家说:无痴是以别境的慧心所为体。《杂集论》上说:‘报、教、证、智,决择为体’,意思是:报是生得的智慧,因为生得善法以宿习为因;教是闻、思的智慧,就是从听闻正法所得的智慧;证是修得的智慧,就是由修习禅定所得的智慧,而智慧是以拣择和决断为其体性。问:如果说无痴的体是别境中的慧,为什么这善心所里,只说一个慧,而不说其余的四个心所呢?答曰:虽然这无痴的体即是慧,然而为表显善心所有殊胜功能,也和烦恼中的‘见’有胜用一样,所以特别彰显来说。
第二家则说:无痴的体并不就是慧,他别有自体,正对治不善中的无明,好像无贪对治贪、无嗔对治嗔一样,都是三善根所摄。《瑜伽论》上说:诸佛的大悲,是无嗔和无痴所摄,并没有说是慧根所摄。无痴既然能摄大悲,可见其体性不是慧。如果无痴是以慧为体,那大悲就不是无嗔、无痴所摄,应该和佛的十力、四无畏一样,属于慧根所摄才对。再者,无痴若真没有自体,那就和不放逸、行舍、不害一样,不是实有的东西了。如此,便违背了《瑜伽论》所说:十一种善法中,除了不放逸、行舍、不害三法是世俗假有外,其余八法都是实有。《集论》上说:无痴是以慧为体,那是因为无痴的因果通于生得、闻、思、修四慧,所以举彼因果显此自性。好像‘忍’是信因,‘乐’是信果,即以忍、乐来表显信的自体一样。
因为贪、嗔、痴是与六识相应的染法,为烦恼所摄,此三者造恶的力量较其余烦恼强胜,所以立它们为三不善根。要断除这三不善根,必须由通、别二种对治。通就是善慧;别就是用无贪对治贪、无嗔对治嗔、无痴对治痴。因为这种道理,无痴应当和无贪、无嗔一样,必定别有自体,才可以对治无明。
论文十一:勤谓精进,于善恶品修断事中,勇悍为性,对治懈怠,满善为业。勇表胜进,简诸染法。悍表精纯,简净无记,即显精进唯善性摄。此相差别,略有五种:所谓被甲、加行、无下、无退、无足,即经所说有势、有勤、有勇、坚猛、不舍善轭,如次应知。此五别者,谓初发心、自分、胜进、自分行中三品别故。或初发心、长时、无间、殷重、无余,修差别故。或资粮等五道别故,二乘究竟道欣大菩提故,诸佛究竟道利乐他故。或二加行,无间、解脱,胜进别故。
讲解:什么叫做勤?勤就是精进。在修善断恶的事上,以勇悍为其特性,对治懈怠,以圆满善法为其业用。勇悍的勇,是表示向善的精进,简别不是勇于染污的恶法;勇悍的悍,是表示精纯无杂,连无覆无记也简别净尽。这就表显精进在三性中唯属善性。
这精进的义相,有五种差别:第一是被甲精进,第二是加行精进,第三是无下劣精进,第四是无退转精进,第五是无喜足精进。这五种精进,也就是经上所说的:有势精进、有勤精进、有勇精进、坚猛精进、不舍善轭精进(注:轭,是车辕前加在牛马颈上的曲木)上面的五种次第,名虽有异,而义实无别。
五种差别外,还有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一初发心,二下品自分行,三中品自分行,四上品自分行,五胜进行。第二种的解释是:一初发心,二长时修,三无间修,四殷重修,五无余修。第三种的解释是:一资粮位,二加行位,三通达位,四修习位,五究竟位。问:三乘究竟无学,既已满足,何以仍须精进?答:二乘的究竟道,是欣向大菩提果;诸佛的究竟道,是利乐有情,所以二乘虽究竟无学,但仍须精进。第四种的解释是:一远加行道,二近加行道,三无间道,四解脱道,五胜进道。
论文十二:安谓轻安,远离粗重,调畅身心,堪任为性,对治惛沉,转依为业。谓此伏除能障定法。令所依此转安适故。
讲解:什么叫做安?安就是轻安。因轻而安,所以能远离粗重,使身心调畅,就堪能胜任一切善法。所以它以对治惛沉为体性,转变身心为业用。也就是说,轻安伏除了能障禅定的惛沉,令所依止的身心,转粗重而为安适。
论文十三:不放逸者,精进三根依所断修、防修为性,对治放逸,成满一切世出世间善事为业。谓即四法,于断修事皆能防修,名不放逸。非别有体,无异相故。于防恶事修善事中,离四功能无别用故。虽信、惭等亦有此能,而方彼四势用微劣。非根遍策,故非此依。岂不防修是此相用?防修何异精进三根?彼要待此方有作用。此应复待余,便有无穷失。勤唯遍策,根但为依,如何说彼有防修用?汝防修用其相云何?若普依持,即无贪等;若遍策录,不异精进。止恶进善即总四法,令不散乱应是等持,令同取境与触何别?令不忘失即应是念。如是推寻不放逸用,离无贪等竟不可得。故不放逸定无别体。
讲解:什么叫不放逸?它是依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四法分位假立,对所断的恶,防令不起,对所修的善,修令增进,就是它的特性;以对治放逸,圆满成就一切世、出世间的善事,就是它的业用。也就是说:即此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四法,对于断恶修善的事,能尽到防修的责任。它没有自己独立的自体,离了以上四法,也就没有不放逸的作用。外人问:信、惭、愧等法,也有断恶修善的功能,何以不放逸不依它们为体呢?论主答:信、惭、愧等法虽然也有防恶修善的功能,但比起精进四法来势用较为微劣,以能生一切善法而论,它们不如三善根;以普遍策励一切善心而论,它们又不如精进。所以不放逸但依精进、三善根为体,不依信、惭、愧等法。
外人问曰:精进只能是普遍的策励善心,而三根只能作为善法的所依,怎能说四法有防恶修善的作用呢?论主反问曰:你们所说的防恶修善的相状是什么样呢?如果普遍依持一切善心称为防恶修善,这就是无贪等三根。如果能够普遍促进善心的增长,这和精进就没有区别。所以防恶修善就是四法。如果令心不散乱就是防恶修善的话,就应当是定。如果令心、心所同取一境称为防恶修善,这与触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使所作善恶忆念不忘称为防恶修善,这就应当是念。按照这种道理推论下去,不放逸的防恶修善作用,离开了精进、三根四法就不可得,所以不放逸肯定没有别体。
论文十四:云何行舍?精进、三根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住为性,对治掉举,静住为业。谓即四法令心远离掉举等障,静住名舍。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初中后位辩舍差别。由不放逸先除杂染,舍复令心寂静而住。此无别体,如不放逸离彼四法无相用故,能令寂静即四法故,所令寂静即心等故。
讲解:什么叫行舍?这是行蕴中的舍,它自己没有体性,也是依精进、无贪三根分位假立的。行舍令心平等正直,不藉加行功用而得安住。它是以对治不平等的掉举为业用,而住于寂静的心境,就叫做舍。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就是分初、中、后三位,来辩论舍的差别,即最初先离掉举、惛沉,使心平等。其次再离谄曲,令心正直。最后不藉加行功用,自然能安住寂静。其能令寂静的是四法,所令寂静的是心、心所。
论文十五:云何不害,于诸有情不为损恼,无嗔为性,能对治害,悲愍为业。谓即无嗔于有情所不为损恼,假名不害。无嗔翻对断物命嗔,不害,正违损恼物害。无嗔与乐,不害拔苦。是谓此二粗相差别。理实无嗔实有自体。不害依彼一分假立,为显慈悲二相别故,利乐有情彼二胜故。有说:不害非即无嗔,别有自体,谓贤善性。此相云何?谓不损恼。无嗔亦尔,宁别有性,谓于有情不为损恼,慈悲贤善是无嗔故。
讲解:什么叫做不害?就是对于一切有情,不去损害恼乱他们。不害是以无嗔为其体性,能对治损害,以慈悲怜愍为其业用。不害就是无嗔,对一切有情不为损害恼乱之事,以此建立不害的假名。无嗔是对治断害物命的嗔心,不害是违反损恼物类的害。无嗔是与有情以乐;不害是拔众生之苦。这不过是无嗔和不害的粗相。在道理上实说,无慎实有自体,不害是依托无嗔一分所假立的。为了表显无嗔是慈、不害是悲二相的不同,一个是予众生以乐;一个是拔众生之苦,是两种利乐有情的超胜力用。
还有这样说:不害并非依无嗔为体,而是自已另有体性。这体性就是贤善,而是以不损恼众生为其业用。论主反驳曰:如果是这样,说那不害的体相不是和无嗔一样吗?怎能另外又有体性呢?对于一切有情不为损恼,因为慈悲和贤善就是无嗔。
论文十六:及显十一义别心所,谓欣厌等善心所法,虽义有别说种种名,而体无异,故不别立。欣谓欲俱无嗔一分,于所欣境不憎恚故。不忿、恨、恼,嫉等亦无。随应正翻嗔一分故。厌谓慧俱无贪一分,于所厌境不染著故。不悭、憍等当知亦然,随应正翻贪一分故。不覆、诳、谄、无贪、痴一分。随应正翻贪痴一分故。
讲解:十一个善心所已如上释,现在是解释颂中‘行舍及不害’中的这个‘及’字,因为在这个及字后面,还包括著欣、厌等十五种善法。这十五种善法,他们虽然与十一善心所的意义不同,然而他们的体性,却是在十一善心所外更无别体。所以不另外安立。
欣是欣悦,是与善欲俱起,它是属于无嗔一分所摄。因为在欢欣的境界,不会生起憎恚。不但是欣,其余的不忿、不恨、不恼、不嫉,也是无嗔一分所摄。因为他们各别正翻的忿、恨、恼、嫉四个随惑,都是属于嗔的一分所摄。
厌是厌离,它和善慧同起,为无贪一分所摄。因为在可厌境上,不会生起染著。其余的不悭、不憍也是一样。这也是正翻小随烦恼中憍和慢两种,属于贪的一分所摄。至于不覆、不诳、不谄三法,是无贪、无痴各一分所摄。因为他们各别正翻的覆、诳、谄三个随惑,是属于贪、痴的一分所摄。
论文十七:有义:不覆唯无痴一分。无处说覆亦贪一分故。有义:不慢,信一分摄。谓若信彼,不慢彼故。有义:不慢,舍一分摄,心平等者不高慢故。有义:不慢惭一分摄,若崇重彼,不慢彼故。有义:不疑,即信所摄,谓若信彼无犹豫故。有义:不疑,即正胜解,以决定者无犹豫故。有义:不疑,即正慧摄。以正见者无犹豫故。不散乱体即正定摄。正见、正知俱善慧摄。不忘念者即是正念。悔、眠、寻、伺通染不染,如触、欲等,无别翻对。
讲解:有人说:不覆,唯属无痴一分所摄,不属无贪。没有那个经论说,覆也是贪的一部分,可见不覆和无贪没有关系。有人说:不慢是属于信心所的一部分,因为既然信他,就不会轻慢他。有人说:不慢是属于舍的一分,因为舍心是平等的,他不会对人高慢。有人说:不慢,是属于惭的一部分,因为惭能崇重贤善,所以不慢。照古德注本:以上三说俱通。有人说:不疑是信心所摄,因为既已相信这个人或这件事,就不会有怀疑。又一种说法,不疑就是别境的正胜解,因其对于已经决定了的正当事理,就不会再有犹豫。又有人说:不疑是别境中正慧所摄,因为有了正见的人,那里还会有犹豫呢?古德说,以上三说俱通。
不散乱是别境的正定所摄,和染见相反的正见,和不正知相反的正知,俱是别境的善慧所摄。和忘念相反的不忘念,就是别境的正念。至于悔、眠、寻、伺四个不定法,他们通于染及不染。就像遍行的触等,别境的欲等一样,善心所中没有与此相对的内容。
论文十八:何缘诸染,所翻善中有别建立,有不尔者?相用别者,便别立之,余善不然,故不应责。又诸染法遍六识者,胜故翻之,别立善法。慢等忿等唯意识俱,害虽亦然,而数现起损恼他故,障无上乘胜因悲故,为了知彼增上过失,翻立不害。失念、散乱、及不正知,翻入别境,善中不说。染净相翻,净宁少染?净胜染劣,少敌多故。又解理通,说多同体,迷情事局随相分多,故于染净不应齐责。
讲解:外人问:六种根本烦恼和二十种随烦恼,为什么有的翻过来就成为善法,有的何以不翻呢?论主答:有的翻过来,性质和作用都有区别,所以各别建立为善。其余的翻过来,性质和作用没有区别,故不一一别立,所以不应有所责难。
还有,一切染法普遍存在于六识的,其作用殊胜,所以要翻过来别立为善。慢等七种根本烦恼(注:七种烦恼为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和忿等九种随烦恼(注:九种烦恼为忿、恨、覆、恼、嫉、悭,诳、谄、害),只与意识相应。害虽然也是这样,但它一再生起,损恼他人,障碍大乘殊胜原因之悲,为了表明它的强胜违害作用,所以要翻过来成立不害善法。失念、散乱、不正知翻过来是念、定、慧,列入别境心所法,并不列入善心所法。
论文十九:此十一法,三是假有,谓不放逸、舍及不害,义如前说。余八实有,相用别故。
讲解:在这十一个善心所中,有三个是假有,就是:不放逸、舍和不害。因为舍和不放逸,是以精进及三善根为体;不害,是以无嗔一分为体。这意义在前面已经说过。除此三法是假有外,其余八法都是实有。
论文二十:有义:十一,四遍善心,精进三根遍善品故。余七不定,推寻事理未决定时不生信故。惭愧同类,依处各别,随起一时,第二无故。要世间道断烦恼时,有轻安故。不放逸、舍,无漏道时,方得起故,悲憨有情时乃有不害故。论说:十一,六位中起,谓决定位有信相应,止息染时有惭、愧起,顾自他故,于善品位有精进三根。世间道时有轻安起,于出世道有舍、不放逸,摄众生时有不害故。
讲解:此下是两家对于善法是否俱起的诤论。第一家说:在十一善法里,有四法是普遍存在于善心中,就是精进和三善根,其余七法则不一定。因为在推寻事理没有决定的时候,不会生信。惭和愧虽是同类,但是惭是依仗自力,愧是依仗他力,依处各别。所以惭生起的时候无愧,愧生起的时候无惭,二者不同时俱起。要到世间道断了粗重烦恼时,才有轻安。至于不放逸和行舍,要到得了无漏道才能够生起。能够慈悲怜愍一切有情的时候才会有不害。《瑜伽论》上说:十一善法,要在六位中生起,即是说在决定位,不能与信相应。能够止息染污的时候,才有自力和他力的惭、愧生起。在善品位,一定有精进和三善根。得到了世间道,才有轻安生起。在出世道的时候,才有行舍和不放逸二法。能够摄护一切众生的时候,才有不害。
论文二十一:有义:彼说未为应理,推寻事理未决定心,信若不生,应非是善,如染心等无净信故。惭、愧类异,依别境同,俱遍善心,前已说故。若出世道轻安不生,应此觉支非无漏故。若世间道无舍、不放逸,应非寂静防恶修善故。又应不伏掉举放逸故。有漏善心既具四法,如出世道应有二故,善心起时皆不损物,违能损法,有不害故。论说:六位起十一者,依彼彼增作此此说,故彼所说定非应理,应说信等十一法中,十遍善心,轻安不遍。要在定位方有轻安调畅身心,余位无故。决择分说:十善心所,定不定地,皆遍善心,定地心中增轻安故。
讲解:第二家认为:前面所说的并不合理:推寻事理未决定之心,信若不生,此心就不是善法,和染污心一样,因为没有净信。至于惭和愧二法类虽不同,那不过是惭依自力,愧依他力,所依的增上缘力有自他差别而已。然而它们的境界都是遍一切善心,并无不同,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假使出世道时轻安不生,这种觉支就不应当是无漏。假使世间道没有行舍和不放逸,其心就不应当是寂静,也就不能防恶修善了,又凭什么来降伏掉举和放逸?既然有漏善心具有精进和三善根四法,世间道就应当同出世道一样,具有舍和不放逸二法。当善心生起的时候不损恼他人,因为违背了能损物的害法,所以才有不害。
《瑜伽论》上说:‘六位起十一’者,那是依增上而说的。十一种善心所法在六位生起,因为在决定位有信生起,在止息染法的时候有惭或愧生起,由于自己的力量而使惭生起,由于他人的力量而使愧生起。在善位时有精进和三善根,在世间道时有轻安生起,在出世间道有舍和不放逸,当对众生怜愍的时候,有不害的生起。
论文二十二:有义:定加行亦得定地名。彼亦微有调畅义故,由斯欲界亦有轻安,不尔,便违本地分说,信等十一通一切地。有义:轻安唯在定有,由定滋养有调畅故。论说:欲界诸心、心所由阙轻安名不定地。说一切地有十一者,通有寻、伺等三地皆有故。
讲解:关于定地,又有两家不同解释。第一家认为,在未到定的加行位,也叫做定地,因为此时也有一点调畅身心的微义,所以欲界地也有轻安,不然的话,便违背《瑜伽论.本地分》所说:‘信等十一,通一切地’的道理了。
第二家说:轻安唯在色、无色界的定地才有,欲界没有。因为由定的滋养,身心才能调畅。论上说:一切心王和心所,由于阙了轻安,所以叫做不定地。至于说:一切地都有十一种善法,那是对初禅的有寻有伺地、二禅的无寻有伺地、二禅以上的无寻无伺地说的,这三地都有轻安。而非欲界所有。
论文二十三:此十一种前已具说,第七、八识随位有无,第六识中定位皆具,若非定位唯阙轻安。有义:五识唯有十种,自性散动无轻安故。有义:五识亦有轻安,定所引善者亦有调畅故,成所作智俱,必有轻安故。
讲解:这十一种善法前已讲过,第七和第八识里,在有漏位全部没有,到无漏位全部都有。至于第六识,在定位全部都有;在不定位只有十种,唯阙轻安。有人说:前五识只有十种,因为它们自性散动,没有轻安。又有人说:前五识也有轻安。如果是定所引的善法,在五识身里也有调畅身心;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的时候,必定是有轻安。
论文二十四:此善十一何受相应?十、五相应,一除忧、苦,有逼迫受,无调畅故。此与别境皆得相应,信等欲等不相违故。十一唯善。轻安非欲,余通三界。皆学等三。非见所断,瑜伽论说:信等六根唯修所断,非见所断。余门分别,如理应思。
讲解:问:这十一个善心所,在苦、乐、忧、喜、舍的五受中,与那一受相应呢?答:有十个都与五受相应,只有轻安一法不通五受,因为逼迫性的忧、苦二受,不能调畅身心,所以轻安一法只能与喜、乐、舍三受相应。
这十一种善法,与别境五法都能相应。因为信等的善法,与欲等的别境,他们的体性并不相违。这十一法,在善、恶、无记三性里唯属善性;在欲、色、无色三界里,除轻安一法不通欲界外,其余的十法都遍通三界;在有学、无学、非有学无学的三位里,则是全部都有。
这十一法,在见断、修断、非断的三断里,都不是见道所断。因为他们不是分别所起的烦恼、所知二障。《瑜伽论》上说:二十二根里的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未知当知根,这六种根,在有漏位是唯修所断;在无漏位那就是非所断了。
第三节烦恼心所
论文一:如是已说善位心所,烦恼心所其相云何?颂曰:烦恼谓贪嗔,痴慢疑恶见。
讲解:上文已经把十一种善位心所讲完。至于烦恼心所,其义相又是怎么样呢?颂文中答覆曰:烦恼有六,即贪、嗔、痴、慢、疑、恶见。
论文二:论曰:此贪等六,性是根本烦恼摄故,得烦恼名。云何为贪?于有、有具染著为性,能障无贪,生苦为业。谓由爱力,取蕴生故。
讲解:以下论文,是解释前二句颂文。论上说:这贪等六个心所,是属于根本烦恼所摄,所以得烦恼之名。什么叫做贪?爱著异熟报果的三有————即三界,及能生三有之因的‘有具’————即惑与业。故贪以染著为性,能障无贪,生起诸苦,就是贪的业用。也就是说,由贪爱的业力,生起了痛苦充满的五蕴身心。五蕴,因取著贪爱而有,又能取著贪爱,所以称五取蕴。
论文三:云何为嗔,于苦、苦具憎恚为性,能障无嗔,不安隐性恶行所依为业。谓嗔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不善性故。云何为痴,于诸理、事迷闇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谓由无明起疑、邪见、贪等烦恼,随烦恼业,能招后生杂染法故。
讲解:什度叫做嗔,嗔是对于三苦————苦苦、坏苦、行苦的苦果,及造成三苦之因的苦具,生起憎恚,以此憎恚为体性,能障碍无嗔,不能安心隐忍,一切恶行依之而起,即成了它的业用。有了嗔恚之心,必定能令身心热恼,一定会生起一切邪恶行为,因为它体性不善之故。
什么叫做痴?对于一切真谛的道理、俗谛的事相,全都迷闇不明,就是痴的体性;能障碍无痴,一切有漏杂染依之而起,就是痴的业用。痴就是无明的别称,由无明次第生起疑、邪见、贪等烦恼、随烦恼,造作恶业,招感后生的杂染诸法。
论文四:云何为慢?恃已于他,高举为性,能障不慢,生苦为业。谓若有慢,于德有德,心不谦下,由此生死轮转无穷,受诸苦故。此慢差别有七、九种。谓于三品、我、德处生,一切皆通见、修所断。圣位我慢既得现行,慢类由斯起亦无失。
讲解:什么叫做慢?就是仗恃自己,以贡高我慢为其体性;能障不慢,生起诸种痛苦,就是它的业用。也就是说:有了高慢,对于三宝净功德法,及超过自己的有德之人,自心不肯谦虚卑下,由此招感生死轮转,受苦无穷。如果详细分析,慢的差别有七种、九种二说。(注:七种慢是:一者慢,对于不胜我的人,固然说我比他强;就是与我相等的人,也说他不过同我一样。二者过慢,不但对于和我相等的人说他不如我,就是对于胜过我的人,也说他不过和我相等。三者过过慢,对于胜我的人,反说他远不及我。四者我慢,就是执有实我及我所,使心高举。五者增上慢,自己才证得少分圣道,便伪称全证。六者卑劣慢,对于胜过我很多的人,说我不过比他少差一点。七者邪慢,分明自己无德,妄谓自已有德。九种慢是:一者我胜慢,二者我等慢,三者我劣慢,四者有胜我慢,五者有等我慢,六者有劣我慢,七者无胜我慢,八者无等我慢,九者无劣我慢。)
论文五:云何为疑?于诸谛理犹豫为性,能障不疑,善品为业。谓犹豫者善不生故。有义,此疑以慧为体,犹豫简择说为疑故。毗助末底是疑义故,末底般若,性无疑故。有义,此疑别有自体,令慧不决非即慧故。瑜伽论说:六烦恼中见世俗有,即慧分故,余是实有,别有性故。毗助末底执慧为疑,毗助若南智应为识,界由助力义便转变,是故此疑非慧为体。
讲解:什么叫做疑?对于一切真实不虚的道理,犹豫不决,就是疑的体性;能障不疑的善品,就是它的业用。也就是说,凡是犹豫不信的人,善法是不会生起的。
关于疑的体性,有两家不同的说法。第一家安慧说:疑是以慧为体,就是对于所观之境,有一种犹豫的简择,所以叫做疑。毗助末底,就是疑的意思。毗是比的意思,助是辅助,末底是慧。合起来就就是比益辅助于慧。既然是辅助于慧,当然就是慧。末底和般若,都是慧的异名,并无别体。所以知道疑是以慧为体的。
第二家护法反驳第一家说:此疑别有自体,能令慧犹豫不决,所以疑并不就是慧。《瑜伽论》上说︰在六个根本烦恼中,除了‘不正见’是世俗假有,属于邪慧所摄外,其余的五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都实有自体,所以疑并不就是慧。如果说,在‘末底’上加一‘毗’字来帮助解释,就说慧是疑的体,那么,‘若南’二字是智,在‘若南’加一‘毗’字来帮助解释,就应当变智为识了。然而,识体并不是智,如何说‘毗助末底’就是慧呢?论文中的‘界’字是性义。
论文六:云何恶见?于诸谛理颠倒推求,染慧为性,能障善见,招苦为业。谓恶见者,多受苦故。此见行相,差别有五:第一种是萨迦耶见,谓于五取蕴是我和我所,一切见趣所依为业。此见差别,有二十句,六十五等分别起摄。
讲解:什么叫做恶见?对于佛教一切谛理,颠倒推度,以染慧为性,能障善见,招感苦报为业。也就是说,有恶见的人多遭苦报。这不过是总略的解释,若仔细分析,这恶见的差别,尚有五种。一者‘萨迦耶见’,译为身见,亦称我见。就是于五取蕴的这个假名不了如幻,执有实我及我所,一切邪见都依我见而起,起惑造业。因此,我见的差别又有二十句、或六十五句,都是属于后天分别起的烦恼。(注:二十句者,是五蕴各有四旬。例如:一、色是我。二、我有色。三、色属我。四、我在色中。如是乃至识是我……,合五四为二十句。六十五句,是计一蕴为我,余四蕴各有三所:一、我璎珞。二、我僮仆。三、我器物。合四三为十二,再加上一个我共为十三。这样推算起来,五蕴有五个我,六十个我所,总合为六十五句。)
论文七:二边执见,谓即于彼随执断、常,障处中行,出离为业。此见差别,诸见趣中有执前际四遍常论,一分常论。及计后际有想十六,无想、俱非各有八论,七断灭论等。分别起摄。
讲解:第二种是边执见,就是在我见之上或者执常、或者执断,能障碍非断非常中道的行相,它的业用,使人不得出离三界苦海。这种边执见的差别,有的主张前际四种遍常论和一分常论:有的主张后际有想十六论、无想八论、非有想非无想八论、七种断灭论。总括起来共有四十七种,这四十七见,都是后天分别所起的烦恼,其中常见四十种,断见七种。
(注一:四遍常论:一、由下品宿住通,能忆前际二十成坏劫自他生死相续,便执我与世间,一切俱常。二、由中品宿住通,能忆前际四十成坏劫生死相续,便执我与世间俱常。三、由上品宿住通,能忆八十成坏劫生死相续。便执我与世间俱常。四、由天眼通,见一切有情死此生彼,诸蕴相续,便执我与世间俱常。这四种,执三界俱常,所以叫做遍常。)
(注二:一分常论:一、有从梵天结束生命而生此世间者,得宿住通,执梵天是常,我是无常。二、执梵王所说:四大种是常,心是无常。三、有从戏忘天结束生命生此世间,得宿住通,执彼天是常,我是无常。四、从意愤天结束生命生此世间,得宿住通,执彼天是常,我是无常。这四种,但执梵天、大等是常,所以叫做一分常论。以上八见四遍常论和四一分常论,都是依过去所起的分别,所以说为前际。)
(注三:有想十六论:一、我有色,死后有想。二、我无色,死后有想。三、我亦有色亦无色,死后有想。四、我非有色非无色,死后有想。五、执我有边,死后有想。六、执我无边,死后有想。七、执我亦有边亦无边,死后有想。八、执我非有边非无边,死后有想。九、我有一想。十、我有种种想。十一、我有少想。十二、我有无量想。十三、我纯有乐,死后有想。十四、我纯有苦,死后有想。十五、我纯有苦有乐,死后有想。十六、我纯无苦无乐,死后有想。)
(注四:无想八论:一、我有色,死后无想。二、我无色,死后无想。三、执我亦有色亦无色,死后无想。四、执我非有色非无色,死后无想。五、执我有边,死后无想。六、执我无边,死后无想。七、执我亦有边亦无边,死后无想。八、执我非有边非无边,死后无想。)
(注五:俱非八论:一、执我有色,死后非有想非无想。二、执我无色,死后非有想非无想。三、执我亦有色亦无色,死后非有想非无想。四、执我非有色非无色,死后非有想非无想。五、执我有边,死后非有想非无想。六、执我无边,死后非有想非无想。七、执我亦有边亦无边,死后非有想非无想。八、执我非有边非无边,死后非有想非无想。)
(注六:七断灭论:认为死后断灭,已无思想,不再转生。包括以下七种:一、我有色,死后断灭。二、我欲界天,死后断灭。三、我色界天,死后断灭。四、我空无边处,死后断灭。五、我识无边处,死后断灭。六、我无所有处,死后断灭。七、我非想非非想处,死后断灭。以上有想、无想、俱非、断灭等三十九见,都是依未来所起的分别,所以说为后际。)
论文八:三邪见。谓谤因果,作用实事,及非四见诸余邪执,如增上缘名义遍故。此见差别,诸见趣中,有执前际二无因论、四有边等、不死矫乱,及计后际五现涅槃,或计自在、世主、释、梵及余物类常恒不易。或计自在等是一切物因。或有横计诸邪解脱,或有妄执非道为道,诸如是等,皆邪见摄。
讲解:第三种是‘邪见’,就是否定善恶因果,无此世间、无彼世间,无世间阿罗汉的实事。以及坚持除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四见以外,其余的一切邪执。好像四缘的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这三缘所不摄的,都归于增上缘摄一样。因为邪见的名义较为普遍,所以摄法亦广。这邪见的差别,有的执著前际所起的二无因论,四有边论,四不死矫乱。有的执著后际所起的五现涅槃。或者主张大自在天、大梵天、帝释天和自性等永恒不变。或者主张大自在天等是产生世间万物之因,或者坚持各种错误虚假的解脱,或者错误地主张以非解脱之道为解脱之道,这一切都属邪见。
(注一:二无因论:一、从无想天下生的人,虽然得宿命通,而回忆不起出无想心以前的生死成坏,便执世间一切都是无因而起。二、由于寻伺虚妄的推求,但能记忆今身之所更事,而不能忆及前身所更事,便执一切都是无因而起。)
(注二:四有边论:一、由于天眼通的力量,能见到下自无间地狱,上至第四禅天,便执世界上下为有边。二、由于天眼通的力量,能忆边傍无有边际,乃生起无边之想。三、由天眼通的力量,能忆世界上下有边,傍布无边,便起亦有边,亦无边之想。四、由天眼通的力量,能忆坏劫分位,便起非有边,非无边之想。这四有边论,因为不计我见断常,所以边见不摄,而属于邪见所摄了。)
(注三:四不死矫乱:一、无知矫乱,有一种无知外道,不肯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唯有这样不说尽天意,死后便能生天。二、谄曲矫乱:有一种谄曲外道,故作神秘的不将自己修证的净天告诉别人,认为这样死后可以生天。三、恐怖矫乱:有一种心怀恐怖的外道,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对别人所问的问题随便解答,认为这样死后可以生天。四、愚戆矫乱:有一种愚戆外道,不回答别人的问题,只是反诘,随人家答什么他都认为是正确的,认为这样死后可以生天。这四种人,因为迷信生天不死,才乱说一通。所以圣教毁之谓‘不死矫乱’。)
(注四:五现涅槃:外道对涅槃有五种错误的认知:一、认为现在欲界所享受的色、声、香、味、触五欲就是涅槃。二、厌恶五欲,以现住入初定便认为是涅槃。三、厌离寻、伺,以现住入第二定便认为是涅槃。四、厌离第二定的喜受,以现住第三定便认为是涅槃。五、厌离第三定的乐受,以现住第四定便认为是涅槃。因为执著于这五种现法涅槃,对于过去来说,是从后际生起的妄见,故称后际五现涅槃。)
论文九:四见取。谓于诸见,及所依蕴执为最胜,能得清净,一切斗诤所依为业。
讲解:见取见,是对于一切恶见及所依的五蕴执为最胜,认为依此能得清净的涅槃果法。由于各执己见,一切外道的斗争都依此而起,这就是见取的业用。
论文十:五戒禁取。谓于随顺诸见、戒禁及所依蕴,执为最胜能得清净,无利勤苦所依为业。然有处说执为最胜名为见取,执能得净,名戒取者,是影略说,或随转门。不尔,如何非灭计灭,非道计道,说为邪见,非二取摄?
讲解:戒禁取见,即依于诸邪见而持戒守禁、及戒所依的五蕴,被认为是最殊胜能得涅槃的清净法。因此,一切外道,或受持牛戒而吃草、或受持狗戒而啖粪,以及拔发、裸体等种种没有利益的苦行,就是戒禁取的业用。
然而有的经论上说,执为最胜的,叫做见取;执能得净的,叫做戒取。这种分法,只是捕风捉影或概略之说,或是随转小乘的方便说法。实则,见、戒二取,都一样的执为最胜和执能得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何以经论上说:不是真正的涅槃,他们以为是真正的涅槃————非灭计灭。不是无漏的圣道,他们以为是无漏的圣道————非道计道。这两种都是第三项的邪见所摄,不是见取和戒取所摄。
论文十一:如是总别十烦恼中,六通俱生及分别起,任运思察俱得生故。疑后三见唯分别起,要由恶友或邪教力,自审思察方得生故。边执见中通俱生者,有义:唯断。常见相粗,恶友等力方引生故。瑜伽等说:何边执见是俱生耶?谓断见摄。学现观者起如是怖,今者我何所在耶?故禽兽等若遇违缘,皆恐我断而起惊怖。有义:彼论依粗相说,理实俱生亦通常见。谓禽兽等执我常存,炽然造集长时资具。故显扬等诸论皆说于五取蕴执断计常,或是俱生或分别起。
讲解:在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根本烦恼中,此六根本烦恼是总,再把恶见分为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五种,此五是别。这总别十种烦恼,贪、嗔、痴、慢、身见、边见六种,通于俱生起和分别起。因为任运而起的叫做俱生起,思察而起的称为分别起,以上六种,无论是任运、思察都能生起。而疑、邪见、见取、戒禁取四种,不通俱生,唯属分别。因为这要由恶友、邪教的影响,和自己的分别才能生起。
边执见中通于俱生而起的,是断见呢还是常见?这有两家不同的说法。第一家说:俱生而起的是断见。因为常见的行相太粗,他必须由恶友、邪教,及自力的分别,才能引生。《瑜伽论》上说:边执见里的断、常二见,那一种是俱生起呢?答曰:断见。何以知断见是俱生起?例如见道以前学现观谛理的人,虽已断了分别烦恼,然而在心理上还这样的恐怖:如果我空,那我和我所,岂不就没有了吗?因此断见是俱生之故,所以禽兽一遇到猎杀它们的违缘,都为死后的我断灭而起了惊怖。
第二家说:俱生唯断的话,那是《瑜伽论》依粗显的行相而说的。若依隐微的理实而论,俱生的断见里,也有常见。何以见得呢?禽兽就是因为执我常存之故,所以才炽然制造巢穴,集积食粮,作为他长期续命的资具,而唯恐我断。因此《显扬圣教论》也说:在五取蕴上的断、常二见,有俱生而起,也有分别而起。并没有不许俱生有常见的。
论文十二:此十烦恼,谁几相应?贪与嗔疑,定不俱起,爱憎二境,必不同故,于境不决,无染著故。贪与慢见或得相应,所爱所陵境非一故,说不俱起。所染所恃境可同故,说得相应。于五见境皆可受故,贪于五见相应无失。嗔与慢疑或俱得起,所嗔所恃,境非一故,说不相应,所蔑所憎境可同故,说得俱起。初犹豫时未憎彼故,说不俱起。久思不决便愤发故,说得相应。疑顺违事随应亦尔。嗔与二取必不相应,执为胜道不憎彼故。此与三见或得相应。于有乐蕴,起身常见,不生憎故,说不相应。于有苦蕴,起身常见,生憎恚故,说得俱起。断见翻此说嗔有无。邪见诽拨恶事好事,如次说嗔或无或有。
讲解:这十种烦恼,那些可以相应呢?贪和嗔、疑,决定不能俱起。因为贪的境界是爱,嗔的境界是憎,爱、憎二境,必定不能俱起。对于疑而不决的境界,是不会有贪著的,所以贪和疑,也决定...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